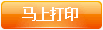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后稷网 > 村委主任网 民俗非遗

老屋门前的大片稻田

换上了不锈钢防盗门的老屋
去年春季,连续下了好几场大雨。家乡有人捎信说老屋快要倒了,我和父亲立马回了一趟家乡。
老屋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县郊以南,坐落于龙源口乡裕富村与峨田村之间的一个小村落内。这个小村落是祖先从南塘新屋分迁过来,三兄弟一起建了六幢六连屋和一个吴家祠堂。房屋构造古典大方,前后翘檐,上有貔貅镇守。屋门上方有五彩绘制的生活图案和花鸟鱼虫,屋内是结实的老杉木雕梁画栋,每间房顶均用九根大小均匀的檩条打底。一房一扇窗,光线充足,房间宽敞。外墙青砖砌,内墙土砖就。前村后巷道路约两米宽,铺以大小形状相似的上千块鹅卵石。鹅卵石排列整齐,深嵌于泥地。每幢屋大门口均有五彩的圆形图,以列队形式延伸向前。在20世纪初,这样的配置是家境殷富的象征。门前屋后大片稻田围绕,祠堂前后也有松树和杉树守护,一年四季中,春夏秋三季掩映在绿色或金色的海洋中。早起见阳光,日落看晚霞,三餐四季,空气清新,舒适得赛似神仙的日子,真是令人羡慕!
后来,吴家祠堂忽然出现大量白蚁,无法清除,渐渐啃空了木结构的祠堂。似乎一夜之间,庞大的建筑轰然倒地。祸不单行,没多久,连在一起的三幢房屋在一天深夜遭了火灾,人们来不及扑灭大火,三幢房屋都烧成灰烬。万幸的是,另三栋隔巷而立的房屋幸免于难。自此以后,吴氏家族开始分崩离析,象征着富有和朝气的“南塘新新屋”只剩下孤单的一排三栋屋。
三栋屋,其实是四栋屋。朝东那幢房屋结构并不是独立式,而是依附于第二栋的庭院式建筑。当年朝东的庭院前门不是轴承式的双开大门,而是商铺式组合门。右侧有个用来买卖东西的窗口,上辈人在此做着南来北往、前村后庄的小本买卖。时过境迁,这房又重归于住房功能。而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在经历过家园被毁、家破人亡的伤痛后,勇敢的祖辈们很快振作起来继续前行,重新回到南塘新屋建设家园。而那被烧毁的三栋房屋被其他四户人家开辟为菜园,人们在此种树、种菜、浇水、施肥……生活重新安定下来,黄发垂髫,鸡犬相闻,怡然自乐,此处人们的生活又如世外桃源一般惬意。
父亲出生时早已家道中落,祖上老人大多已离世,奶奶作为老二孙子辈唯一独苗,在祖奶奶及族人的安排下,相中了来自安徽的在城里任工商所所长的爷爷,两人结为夫妻,伉俪情深。祖奶奶23岁便开始守寡,但也留了些金银细软,以及祖屋等不动产,加上爷爷在城里工作,一家人的日子也算过得殷实富裕。父亲的出生,让三代人喜不自胜,家族里的长辈们对他呵护备至,父亲在富足又幸福的环境中长大。
我和父亲在村口下了车。一眼望去,老屋像三位年迈的老人,手挽手站立在稻田中央,虽然中间那幢房屋的屋顶倒塌了一半,却依然不改以往气势,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感觉。房屋后的墙面写着“农业学大寨”“大干快上”的标语,字迹虽模糊,但依稀可辨。记得小时候,村首村尾的农家屋墙壁上都有红漆标语,这是乡村的标配。
踩上凹凸不平的鹅卵石,仿佛回到了从前亲切而温馨的岁月。鸟儿在头顶鸣啾,小草在阳光下摇摆,风儿轻轻吹拂。看着暖洋洋的春光里的老屋,记忆有刹那间的错乱,好似穿越回童年时光。
小心开启生锈的铁锁,轻轻推开沉重的木门,仿佛在亲近一位百岁老人,那被时光剥落的繁华,裸露在惨白的时间外壳,似在无声诉说着岁月的雨雪风霜。随着木门“吱呀”一声,便打开了过往的生活场景。我和父亲一边伸手拂去扑面而来的蛛网,摸索前行,一边四顾张望。走了几步,仰头便瞧见屋顶几处大块亮光,那是屋瓦掉了,或是被风吹散了,阳光雨水趁机溜了进来。在这无边沉寂的、黑暗的屋里,经过漫长的时光与风雨的洗礼,堂屋的天花板渐渐显出大片濡湿与黑斑,那是被冷落后的痕迹与挣扎。堂屋进门处的天花板上,一只凤鸣朝阳的雕花板也被雨水浸透,上面的凤凰已不知去向,但那朵硕大的牡丹依旧绽放于天花板一侧,经典古韵让人仰望,令人敬佩不已。正中摆放的方桌因雨水浸泡,桌脚脆弱得好像用手轻轻一碰就会断成两截。右侧下厢房漏水更严重,大块房板掉落,一抬头就能看到天空,感觉只要大声说话,房板随时会掉下来一般,摇摇欲坠的样子着实令人害怕。我们继续往里走,里面的家具大多搬走了,但旧时的痕迹依然在。每走一步,记忆都与儿时的光阴重合。昔日贫穷困苦的岁月,儿时无忧无虑的欢乐与嬉闹的记忆,那些成长与磨难的时刻,就这样被波涛般汹涌而来的时光淹没。
父亲说,我小时候就是一个爱劳动的小家伙。刚过三虚岁,就知道打扫堂屋,只不过没扫两下,自己先被扫帚绊倒了。那时,父母跟爷爷奶奶分开吃住,西边第一幢堂屋右侧的小土灶台和放柴火的茅窝,成了我们一家三口的简易小厨房。堂屋的连房是由木板隔成的,如今门首旁边的木夹板上,还有我用木炭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字,那时的童言稚语如今读来依然让人忍俊不禁。
这幢老屋原先住了两户人家,左侧三间屋住的是同宗高二辈的一家六口,据说是借住在我们家的。他们家辈分大,父母要称他家的小孩为叔叔,我们小孩称他家大人为老爷爷,称小男孩为爷爷。我的爷爷奶奶住第二幢屋左侧和连房,住右侧的同宗爷爷去了城里,爷爷奶奶便把它们用来放茅草。第三幢的老爷爷跟邻居同辈,院式房里住的是第三幢爷爷的同房侄子,我们都要称其为爷爷的。三栋屋里的住户是一个祖先三兄弟的家人,我家辈分最小,但是开枝散叶最多。在那些困难时期,这几家人如同一家人。
小时候,母亲除了去队里干活,农闲时还要去三十里外的七溪岭砍柴。家里洗衣服、喂猪、喂鸡、带妹妹的任务全交给了我。母亲在出门前总要把所有的活叮嘱一遍,害得我以为又加了活,哭着跟在母亲身后,从大门口一直嘟囔到屋后,站在那里看着母亲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山脚下的层层树影里。
儿时最开心的还是和村里小伙伴趁大人出工,一起蹲在大门口的石凳旁用沙子捏米果、用竹杆捕蜻蜓、打叠手过家家、在大床上披床单唱戏的欢乐时光……三五成群,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那是我们怀念的童年时光。
春天一到,门前的稻田里全插上了秧苗,门口的田埂上也都种上了竹篱笆。清洗干净的衣物全都晾晒在篱笆上,远远看去,像五颜六色的旗帜在风中飘扬。门前有三个菜园子,各家把地基辟为菜园,各占了几间房整成几垄土,种各种蔬菜,青椒、茄子、冬瓜、南瓜、苦瓜、丝瓜,也有峨眉、春麻、空心菜。墙角也被大爷大妈种上了橙树和橘子树。春天,门前春意盎然;夏天,篱笆五彩缤纷;秋天,稻田硕果累累;冬天,稻田一片空旷阔达。
门后有一条小溪,雨水多的时候,在睡梦中都能听到鱼儿上水的“噼哩啪啦”声。稻子抽穗时,风一吹,满屋子都是稻花香。双抢时节,走出房屋,一抬眼就是一片金色的海洋。天蒙蒙亮,就能听到早起的农人收割稻子的“唰唰”声和说话声,以及听到牛在收割了的稻田里滚耙时“哞哞”的叫唤声。包产到户到来后,我们这些孩子也懂得用劳动创造财富和粮食,知道了忙碌与充实的快乐。
夏天的夜总是那样凉爽惬意。劳累了一天的男人,总要跑到一里外的泉水洲,扑进清凉的泉水里,洗净身上的汗水和泥污。晚饭后,大家拿着板凳齐聚在小村口,吹着从田野吹来的清凉的风,抽着自家种的草烟,摇着宽大的蒲扇,聊着家长里短。小孩子一开始在旁边跑着跳着捉萤火虫,后来又去数星星,最后依偎在父母身旁慢慢进入梦乡。

老屋的房顶铺上了时下流行的红琉璃瓦
秋天,门前被父亲用水泥硬化成一块小小的晒谷坪,将收回来的稻谷倒在上面晾晒。看着金黄的稻子,就像看到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稻田里的稻草被人们扎成草垛子,分脚站立成人字形,沐浴着秋日阳光,也饱饮着秋风与冷露。秋高气爽,蓝天白云,抬头望去,天地仿佛都近了。
冬天窗外一片萧瑟,寒风从西边呼啸而来,冷得人直打哆嗦。勤劳的母亲早已备好过冬的毛衣与棉袄,储藏了足够的柴火与炭火,地里的番薯收进了仓,稻子晒干藏上了楼,天晴时晒晒衣物,下雨时坐在火盆旁纳千层鞋,间歇跟邻居唠唠嗑。哪管屋外东南西北风,苦中作乐也逍遥。
时光远去,三幢老屋依旧。它们吸收了日月精华,饱受了风雨雪霜,见证了迭代繁华,养育了子孙后代,它们依旧安然耸立,似乎有使命完成后的松弛,只在静等大限来临。可是,我们难道真的要让见证了多年光阴的老屋,见证了几代人繁衍生息的家乡,消逝于时光的洪流中?如果我们梦回的地方不再存在,又哪来子孙后代的传承与发扬?
回来后,我把老屋的情况告之远在深圳工作的两个弟弟。已在深圳定居的弟弟一致要求尽早拆除,以免老屋倒塌发生危险。而年过七旬的父亲犹豫不决,我明白,他是不忍心让旧时光阴与昔时美好倒伏于时光的瓦砾无处寻找。于是,我同意了老父亲保留老屋,重新修缮的决定。
父亲请人把屋顶的灰瓦撤下,改用时下流行的红色琉璃瓦,把大门屋檐处开裂的部分重新加固并粉刷一番,拆除木大门,换上最新潮的不锈钢防盗门,将老屋内所有墙面地面都粉刷一新,窗户全换上铝合金窗。老屋焕然一新。我把修缮后的照片发到家族群,群里顿时热闹开了,大家都说父亲这事做得漂亮,这一举动完美保留了我们儿时的记忆,也让游子的乡愁有了安放的地方。
父亲说,时光荏苒,即使生活改变,老屋也始终是祖辈的根。只有保留了咱们的根,儿孙才会常回家看看。你说,这样的老屋还“老”吗?它重获新生,永远年轻。

老屋一里外的泉水洲
责任编辑:武凯
原文地址:http://www.cwzrzz.com/html/2024/0311/629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