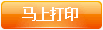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后稷网 > 文化产业网 往期 文化传承
关于道德在人性中是否有根基的问题,孟子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即“人性善”。遗憾的是,这一观点历来备受争议,没有得到正解,或是理解为人天生就有实然的德性,或是理解为人有向善的可能性,但实际上,“人性善”是指人有本心,而本心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具有价值自觉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孟子将价值尺度论证为价值真理,规定了人的本质。
“人性善”即人有“本心”
关于道德在人性中是否有根基的问题,早在先秦时代就被激烈地讨论过。告子认为没有,认为人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不善,“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但孟子认为有,并直言人性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到底孰是孰非呢?
告子之所以说人性无善无不善,是因为他说的“人性”是指人生来就有的欲望和本能,即“生之谓性”。对于生来就有的自然禀赋而言,当然不能用“善”和“恶”这样的道德概念对其进行判断,就像我们不能把“一次地震”称为“恶”,而把“一场春雨”称为“善”一样。但孟子并不认可告子,他认为如果“生之谓性”,“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换言之,告子泯灭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孟子主张应该从这一区别,即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几希”处来论人之性。那么,这“几希”是什么呢?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由上可知,这“几希”就是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即仁、义、礼、智四端,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如果没有,就是“非人”。另外,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原来孟子所谓的性善,并不是指人性中已经有了仁、义、礼、智四种德性,而是说人性中已经有了这四种德性的“种子”,有了发展此四种德性的能力,即恻隐、羞恶、辞让和是非之心。因此,孟子的性善论,也可称之为心善论。
孟子是如何确定作为人之性的“几希”的呢?从引文中看,孟子首先确定的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接着,孟子直接由此出发而推论出,人有羞恶、辞让和是非之心。这一推论常被人诟病,被认为根本不符合逻辑:要说人人都有不忍之心,那还勉强能使人同意,因为似乎同情心是一种本能,但要说人人都有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却太夸张了,一点也不符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此,我们要为孟子辩护一番:第一,上述误解其实仍然建立在“生之为性”的基础上,从自然禀赋来说,同情心确乎是一种本能,而其余的“三心”确实没有。但孟子是反对“生之为性”的,他说的“几希”绝非人生来就有的某种自然禀赋,也不是通过比较人与动物的生理学特征来确定的。第二,孟子专门举了“乍见孺子将入井”的例子来阐述不忍之心如何显露。“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数句,说明救助行动完全与利害关系的考量无关,而是心之自身直接呈现的结果。由于此时的“心”不受利害欲望的裹挟,而真正属于心自己的活动,因此被孟子称为“本心”(《孟子·告子上》)。换言之,孟子举不忍之心显露的例子,是为了说明“本心”的存在,“不忍之心”只是“本心”显现的一种方式。紧接着,孟子就列举了“本心”显现的其他方式,比如“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只要做这样的理解,孟子的推论逻辑就顺理成章了。
既已确定“本心”是心的独立活动,我们还可以确定的是:“本心”是直觉、情感的心,而不是逻辑、理性的心,因为“本心”的呈现方式是“乍见”,是“怵惕恻隐”。当然,这一确定还只是停留在“本心”活动的“形式”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独立活动的“内容”是什么?从“本心”呈现的几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出“本心”是一种“价值尺度”或“价值权威”,它能随时随地地对经验活动中的事象进行价值判定,并显现为一种情感上的反应态度。基于此,劳思光将其称为“自觉心”,即对价值的自觉,对“应该不应该”的自觉。比如,“恻隐”是“人对生命之苦难或毁灭所起之‘不应有’之自觉”;“羞恶”是人对某种事象,觉其不应该有,而“显现据斥割离之自觉”;“辞让”是人在考虑自己的所得时,对应得或不应得之自觉;“是非”是人对一切主张之合理或不合理之自觉[1]。由此可见,孟子所谓的“人性善”其实就是指人心本有此价值自觉之能力,而这一能力本身包含着仁、义、礼、智四种德性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孟子称这一价值自觉能力为德性之“端”。要使德性能够充分展开,还须一种存养功夫,因为人能自觉到善恶,并不代表人在现实生活中就能为善去恶。所谓“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以往有注解者,将孟子的“性善论”理解为人有向善的可能性,或者将“性善论”理解为一种“假设”。但孟子说得很清楚,“人之有此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四体”怎么会是一种可能性,或是一种“假设”呢?它当然是一种实然存在的东西,但这实然存在的东西,并不是指德性的实然存在,而是作为德性之根基的“自觉心”实然存在。劳思光将孟子的“本心”解释为“自觉心”,无疑是把握住了孟子“性善论”的核心。遗憾的是,劳思光的理解仍然是不充分的,这一点将在后文详论。
恶来源于“本心”之被遮蔽
对于“性善论”,人们往往会提出一个问题,即所谓“恶”的来源问题。既然人性都是善的,那么恶从哪里来呢?在对孟子进行这样的提问之前,我们要先对这一提问本身进行考察,以便我们能够理解我们到底对孟子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很明显,对“性善论”提出恶的来源问题,是基于以下理解:即“善”是一种实然的德性。既然“善”是一种实然的德性,那就必然已经去除了“善”的反面“恶”,那么恶从哪里来呢?孟子的“性善论”是否存在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呢?从表面上看,似乎如此,孟子在与告子辩论时说:“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就这一段引文而言,孟子的“势”,类似于卢梭的“社会”,是“势”改变了水的流向,同样也是“势”使人行不善。然而,事实上这一问题在孟子那里并不存在,因为孟子所说的“人性善”并不是指人已经有了实然的德性,而是说人有了发展出实然德性的根基,即“本心”。因为有“本心”,所以“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既然,为不善并不是才之罪,那是谁之罪呢?
孟子继而指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
这里的关键是对“思”的理解,孟子称之为“心”的机能,而“心”正是指“本心”;所谓“思”并不是指“思考”,也不是指“反思”,而是“自觉”,可以将其比喻为“价值之光”。“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并不是说“本心”有时能“自觉”,有时不能“自觉”,“自觉”时,人就行善,不能“自觉”时,人就行不善。作为“价值之光”的“本心”是常在的,也不曾“熄灭”过,但却有被遮蔽的时候,如果被遮蔽,就是“不思”,就会行不善。
那么,“本心”如何会被遮蔽呢?因为“本心”的发用,要借助于“身”,但“身”作为生理体,有追求外物的需要,并且“身”没有“思”的功能,一旦与外物交接,“身”就容易忘记“本心”的指示,而专注于对外物的追求,这样一来“本心”的“光”就被“身”的物欲所遮蔽了,可见,孟子所说的“势”,其实就是“身”的物欲。“身”虽然有遮蔽“心”的可能,但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没有“身”,“心”的发用也就失了着落,或者简直可以说没有了“心”,因此,孟子并不主张“身”的欲望就是“恶”。只有“身”的欲望脱离了“心”的主宰,才会成为“恶”,孟子称之为“养小以失大”(《孟子·告子上》);但只要“身”的欲望得到“心”的主宰,那么“身”的活动也就是“心”的活动,所谓“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孟子·告子上》)。也正是基于此,孟子在政治上才主张“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因为如果“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
“本心”中蕴藏着价值真理
我们已经反复提到,孟子讲“人性善”,并非指人性中有实然的德性,而是说人有“本心”,即“本心”是善。关于“本心”,儒家的学说中还有其他称谓,比如《大学》中称其为“明德”,朱熹称其为“天理”,王阳明称其为“良知”或“至善”。这些称谓都说明了在人心中本有“价值尺度”,可作为道德的根基。上文中,我们提到“本心”时,多指“本心”的自觉性能,即“本心”作为“价值尺度”所发挥的功能是,随时随地就现实生活中之事象作出价值判断,故而也将“本心”称为“自觉心”。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本心”作为“价值尺度”本身到底是什么?
依孟子,“本心”即善,那么,何为善呢?孟子答曰:“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因此,问“本心”作为“价值尺度”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在问,对于人来说,到底什么才是可以欲求的?简单来说就是在问:人之为人的目的是什么?问“什么是人可以欲求的”似乎有点奇怪,不是应该问“什么是人应该欲求的”吗?“可以欲求的”看起来是在事实层面进行追问,而“应该欲求的”好像才是在价值层面进行追问,通过对前者进行提问,怎么可能得出关于“价值尺度”的答案,得出关于“人之为人的目的是什么”的答案呢?然而,在孟子那里,“人们欲求什么”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人们可以欲求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问题,用“可以”而不用“应该”,是孟子觉得自己讨论的是价值真理问题,而不是在讨论价值选择问题。那么,什么是人可以欲求的呢?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
可以看出,孟子所谓的“可欲”,其实就是“求在我者也”。何为“求在我者”呢?就是我欲求的东西能不能得到,是完全由我自己做主的,而不受外界的影响,如果我决心去求,那就一定能得到,如果不去求,那就肯定得不到,这里面没有丝毫运气的成分,因此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从日常生活来看,人们大多追求的是功名利禄,那么功名利禄属于“求在我者”吗?在孟子看来,功名利禄属于“求在外者”,是“求之有道”,但“得之有命”的。同样的话,孔子也讲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可见,功名利禄、富贵穷通,皆不“可欲”,皆不是“求在我者也”。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才属于孟子所谓的“求在我者”呢?简单的回答是:“德性”。而“德性”在儒家那里也可以用“仁”来概括。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正因为“仁”是“求在我者”,所以,我便能求仁得仁,如果没得到,那说明我做得还不够,因此“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反过来,“仁”并不是外在于人之行动的一种结果,而恰恰就是行动本身,因为如果是前者,那便不可能属于“求在我者”,毕竟外在于行动的结果,总是不能完全由人来主宰的。由于行动本身即“仁”或“非仁”,因此,所谓“得仁”即“做仁”,当下做,便当下得,而不是做而后得。于是,追问“什么是人可以欲求的”,就转变为追问“什么才是人的行动方式”。而人的行动方式问题,即做人问题或“做仁”问题。
那么,何为“做仁”呢?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概而言之,“亲亲”“仁民”和“爱物”,在孟子那里就是价值真理,是人之为人的目的。这里的关键是,孟子在这里并不是说“亲亲”“仁民”和“爱物”是好的价值,而是人们应该选择这一好的价值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来赋予生活以积极的意义。孟子并不是在“劝善”,而是在陈述一个价值真理,“亲亲”“仁民”和“爱物”就是“作为人的人”的存在方式,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对“作为人的人”的否定,只能成为“作为自然的人”,这就是孟子的人禽之分。价值真理并不能强迫人们去践行它,但它告诉人们,如果不做,人的目的就没有达到,人生就留有遗憾。这一价值真理,在孔子那里被表述为:“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斯道”即人道,而人行人道才成为人,人道是人本然的存在方式!由此出发,我们就能看到劳思光将“本心”理解为“自觉心”,依然有不充分的地方。劳思光对“自觉心”有这样一番解释:人在自觉生活中,时时有“应该不应该”之自觉;不论人所具之知识如何,以及人持何种内容之价值标准,总之,人必自觉到有“应该不应该”。此种“应然”之自觉,与利害考虑不同。人当离开利害考虑之际,仍有此种自觉[2]。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劳思光将“自觉心”形式化了,“不论人持何种内容之价值标准”,“人必自觉到有‘应该不应该’”。然而,孟子的“自觉心”是包含明确的价值标准的,即“亲亲”“仁民”和“爱物”,并不是任何内容之价值标准都可以。笔者认为这一点正是劳思光疏忽的地方,这一疏忽来源于他偏向于从功能方面来理解孟子的“心”,而没能从“心”的功能见到“心”的本体。
参考文献
[1][2]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责任编辑:史偌霖
原文地址:http://www.whcyzzs.cn/html/2022/0331/410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