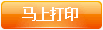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后稷网 > 文化产业网 往期 影视表演
作为“新力量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1],学院派出身的导演路阳自长片处女作《盲人电影院》(2010)亮相以来,他的一系列创作颇受外界关注与好评,从《绣春刀》(2014)、《绣春刀Ⅱ:修罗战场》(2017)到《刺杀小说家》(2021)均有不俗的表现。其中,路阳“五年磨一剑”打造的于2021年公映的影片《刺杀小说家》更有了新的气象与突破。
本文以路阳执导的影片《刺杀小说家》为研究对象,通过题材、叙事、主题、人物、视听语言等方面分析导演的创作手法和创作理念,进一步阐述作品中的核心旨归和人文意蕴,并探究在本片奇幻、瑰丽、多元的风格包裹之下,路阳导演感性与理性兼具、不拘一格的创作风格和融贯东西、立足本土的美学追求。
创作主题与导演理念
影片《刺杀小说家》融合了奇幻、动作、悬疑、武侠、冒险、伦理等类型元素,以双主角结构、双线并置交织的形式讲述了丢失爱女的关宁与落魄的作家路空文面临不同的人生困境,在命运的安排下产生交集,最终二人携手抗争,分别完成寻女与复仇的故事。
边缘化的主角,“信念”主题与“镜像”叙事
导演的创作动力、手段、态度统摄于导演理念,具象化地表现于创作的人物、主题、视听语言等环节中。正如安德烈·巴赞所说:“要更好地理解一部影片的倾向如何,最好先理解该影片是如何表现其倾向的。”《刺杀小说家》中关于“信念和希望”的主题,在路阳之前的创作如《绣春刀》(2014)、《绣春刀Ⅱ:修罗战场》(2017)中也一以贯之,这正是激发他此番创作的内驱力。路阳导演被原著小说中的两位主人公打动,在自己的创作中将边缘人塑造为影片的主要角色,自然流露出了创作者的人文关怀以及同为创作者的感喟与共情。
影片现实世界的双主角之一关宁,自从丢失挚爱的女儿,一心寻女多年而到了偏执、歇斯底里的地步,为了寻找女儿,他失去了婚姻、工作、自我乃至一切,将自己放逐为社会的边缘人;另一位主角是父亲意外离世,自己一无所成、潦倒失意的作家路空文,他孤僻、疏离,写作成为他生命的全部。阿拉丁集团老板李沐指使屠灵找到关宁,以找回关宁女儿的关键线索为要挟,利用关宁的“超自然”能力要求他刺杀路空文。接受任务的关宁在与作家路空文的相处中逐渐认识到路笔下的异世界对现实世界会产生实际影响,也意识到了李沐与路父之死有关。随着叙事的深入,当关宁发觉李沐的阴谋时,关宁面临着选择。最终,关宁选择保护路空文。路空文续写小说,令异世界的红甲武士成功“弑神”,救回了小橘子,在与异世界互为镜像的现实世界中,关宁得以找回丢失的女儿。
影片以人物的行为动机和冒险历程铺陈情节,展开双线叙事。在平行的叙事脉络中,这两个主要角色在两个世界中都有各自的执念和追求,推动两个世界的叙事线发展。最终两个世界重叠,两条叙事线融合在一起,将叙事推向高潮,两个主角在各自的选择中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影片在符合人物行动逻辑的叙事中自然地成就角色的华彩,点明了主题“只要相信,就能实现”。对于这一主题,电影观众能调动日常生活中的丰富经验与之共情,并相信这个故事,沉浸在电影中。
观众为先与“作者性”
“我希望能够让观众忘我地投入这部电影,这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2]在路阳的电影创作观念中,让观众相信他的电影成为他自觉的追求。“我所喜欢的方式,是尽可能在电影中去减弱,甚至去隐藏所有的存在痕迹和存在方式,其中也包括摄影机的存在感、剪辑的存在感、表演痕迹的设计存在感和导演意识的存在感。”[3]巴赞曾指出,“蒙太奇的运用可以是‘觉察不到’的”“在这种影片中,镜头的分切目的无非是为了按照一场戏的实际逻辑和剧情逻辑来分解事件。正是它的逻辑性才使这种分解显得不易察觉到,观众的思路自然地与导演向他们提供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因为导演的观点是由动作发生的地点或戏剧注意点的转移所决定的”[4]。但是在高度假定性的影片中,这种“透明”的叙事观念不容易实现。在利用电影的幻觉机制使观众保持沉浸感的同时,路阳也葆有“体制内作者”的“锐利之气”。
在作家路空文的小说《弑神》中,异世界不仅真实存在,而且会切实影响他与关宁所在的现实世界,影片设定的双重世界实际存在着互文关系。两个世界作为顺时同步的平行时空,互为因果,互为镜像。电影取材的新意恰恰关乎双重世界的设定,这也是影片创作的难点和重点所在,尤其是要让观众接受小说能影响现实世界这一观念,从而接受故事设定,进入故事。路阳导演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影片引入异世界的方式。小说的虚构性会让观众产生异世界是虚构的印象,进而认定双重世界一个为真,另一个为假,影响电影的叙事目的和叙事效果。所以导演在构思之初就注重异世界独立性、真实感的塑造,在异世界首次出现时没有采用借助小说文本来呈现的方式。电影开篇在短时间内高效地呈现了双重世界,暗示了两者的关联和影响。当“小橘子”的画外音喊出“爸爸”时,画面给出了更多异世界的信息(原始密林、云中城),随后以关宁从梦境中醒来过渡到现实世界,关宁重复台词“城里边有”,抛出悬念。在下一个场景中,导演设置了关宁在超远距离以“超自然”的能力投石逼停人贩子货车的情节,让观众一下子就能接受这个现实世界也颇具奇幻色彩的设定。
创作时,导演以观众为先而不乏“作者性”的创作观念也体现在了影片中。影片没有采用严格的闭环结构,而是让剧情随着人物的动机、逻辑和机缘“自然”生发,体现出了东方式的哲学和美学观。在双线并置交织的结构中,并不存在闭环结构可预见的逻辑,因此能更积极地激励观众跟着主角一起冒险、体验和做出选择,享受影片带来的快感。
保持观众幻觉,让观众相信电影,体现出路阳作为创作主体的自反和思辨,他的电影理念无不渗入创作的各个细节中。路阳认为:“电影创作肯定需要使用一定的手段和技巧,也一定会有设计,但是,我还是希望在我们创作的作品中,能够把这些东西都藏起来……最终我们其实需要达成的目的是,能够让观众忘掉我们的存在,只是去关心这个故事,去享受这个电影本身。”[5]这是路阳作为电影创作者秉持的“信念和希望”,也是他对路空文这一角色的反身自问和对《刺杀小说家》影片主题的重申。
风格追求与美学表达
路阳追求“隐藏电影手段”的创作观念使他专注于讲好故事,挖掘叙事的内部逻辑和情节细节,保持观众幻觉,从而引导观众充分理解故事、相信故事,在美学上实现沉迷的效果。也正因如此,《刺杀小说家》奇幻、瑰丽、多元的风格包裹之下蕴含着路阳感性与理性兼具、不拘一格的创作风格。影片融合了多种类型元素,尤其融入了路阳导演情有独钟的武打动作风格,构成了丰富的视听奇观。在《刺杀小说家》中,导演路阳将表现形式注入每一个场景和段落中,形式与内容整合圆融,相辅相成,通过形式进而营造出影片的情绪与氛围,传达出独特的创作风格与美学品格。
双重空间的影像表征、隐喻与张力
影片叙事要求呈现现实空间与异世界两个世界,导演设定了在写实情怀与浪漫主义的风格中两者必须兼具“真实感”,他相信真实感会带来另外一种力量。主要依靠CG搭建出来的异世界,借助画面和声音共同建构了复杂多元、层次丰富、完整自足的宏大场景,满足了观众对视觉想象力的消费需求。同时,异世界的视觉奇观中也有对真实感的考量,从而让观众相信异世界的存在及其影响现实世界的力量。
路阳将现实世界设置在山城重庆,在空间上向互为镜像的异世界空间靠拢,也为实现两个世界自然流畅的转换与过渡服务。重庆奇异多变、丰富立体的空间特征赋予了影像独特的空间表征与空间美学。陡峭的地势、浑浊的江水、曲折的陋巷、浓重的雾、潮湿的空气和冬季仍有绿意的植被等意象,共同营造出了疏离、悬疑的氛围。蓝绿的色调和阴冷中的暖色,使得现实世界蒙上了一层“超现实”的奇异质感。在色彩创作上,影片调色历时一个多月,使两个世界在视觉上呈现出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分的艺术效果。
双重世界交织呈现增加了叙事的复杂程度,路阳以沉稳的导演风格完成了影片流畅的叙事,主要运用四种方式实现两个世界的过渡与转换(有单独使用或组合使用等不同情况):1.利用相似的景别和镜头角度;2.利用相似的意象;3.运用声画对位的手法,使用画外音引入另一个时空;4.利用两个世界中对应的角色,如路空文和少年空文。
此外,在双重世界中,导演借助声音和画面,通过隐喻手法传达出了更深层次的意义。例如,在具有强烈空间感的现实世界中,城市的空间意象帮助导演完成了符号的隐喻意义。当关宁跟踪作家路空文时,两人第一次同框,分别走在交错而尽头汇于一处的建筑物(天桥)上,画面隐喻二人终将汇聚的命运。又如,导演在强化两个世界的互文关系,利用声画对位的方式进行双重世界的转换时,也运用了“寓言性”的隐喻:黑甲对少年空文说,“你看那,赤发鬼就在那儿”,对应的画面为异世界的“云中城”,继而画面变为现实世界中的都市远景,李沐的画外音响起“七八年前,我从闸北到黄埔……”,从而实现了时空的过渡,并且这个过程暗示了观众,使观众将现实世界中操弄民众的李沐与异世界中代表威权的神(赤发鬼)的形象重叠了起来,赋予了影片寓言性和启蒙的意味。
从美学角度看,现实世界的写实风格中有奇幻色彩,异世界的高度假定中包含了写实韵味,两个世界各自较好地平衡了真实中的假定与假定中的真实,这种张力贯穿于整部影片中,彰显了影片浓重的艺术气息与艺术底色。
电影数字技术革新与中国传统美学追求
《刺杀小说家》的开创性不仅体现在采用平行时空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互为镜像的叙事结构,这是中国电影史上不曾有过的,还体现在不同以往的创作观念和视觉效果呈现上。这让路阳在“新力量导演”中也显得十分亮眼,他不囿于当下电影行业的创作惯性,带着“作者”的反叛姿态和对电影数字技术的革新观念寻求创作突破。“我们并不是想用传统的方法去拍一部视效电影,它既不是好莱坞体系,它也不是中国电影以前讲故事用过的方法,我们希望无论从故事手段还是视觉上都是新的。”因此,路阳也是一位主动寻求数字技术支持来突破创作限制,具有丰富艺术想象力的“技术型”导演。
《刺杀小说家》全片视效镜头有1700多个。影片开创性地将动作捕捉、面部表情捕捉、前期预览虚拟拍摄和实拍阶段虚实结合拍摄等多种数字技术整合进真人电影的拍摄中,其中完整使用虚拟拍摄技术在中国电影产业中为开先河之举[6]。在新的技术条件支持下,导演在视觉效果、风格和美学上不拘一格,追求融贯东西、立足本土,结合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使影片既创新,又呈现出传统的东方审美意趣。如异世界的构思搭建,吸纳糅合了魏晋风格以及唐和宋的元素,打造出了一个古代的东方世界。又如在类人生物角色的视觉设计上,借鉴了济斯瓦夫·贝克辛斯基的画作风格;赤发鬼的形象呈现则在利用面部表情、动作捕捉技术之外,艰难地实现了毛孔随着皮肤拉伸而运动的效果,使数字角色更“逼真”,更呈现出了创意十足的激烈打斗。其中,黑甲与主角少年空文的关系从黑甲寄生空文、空文能控制黑甲到二人成为“伙伴”,一系列变化让人印象深刻,导演还为黑甲设计了诙谐有趣的声音和对白,使之富有个性。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类人生物角色与真人演员一起对戏的场景:如黑甲在雨中的打斗戏,导演利用多角度的主客观镜头、高低镜头、升格镜头、游戏化运镜、手持镜头等手段灵活流畅地进行了展现;整部电影的重场戏,即少年空文与神(赤发鬼)对峙的场景,导演用画面营造环境氛围,具象地彰显了影片探讨人与命运的关系这一主题,引人深思。
《刺杀小说家》可以说是在“第四消费时代”的经济社会语境下应运而生的[7],满足了“网生代”“游生代”受众对“想象力消费”的巨大需求。导演路阳以开拓先行的自觉意识与行动驱动创作,游走于类型之间而不乏“作者”气质,因而该片也极具开创性。导演根据题材、叙事、场景、角色等方面的创作要求大胆创新、锐意进取,在数字技术层面上提出了诸多挑战,最终完成的影片《刺杀小说家》推动了中国电影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也为建构中国电影工业美学理论贡献了一个成功的案例。
参考文献
[1] 陈旭光.新时代 新力量 新美学——当下“新力量”导演群体及其“工业美学”建构[J].当代电影,2018(01):30-38.
[2] 路阳,孙承健.《刺杀小说家》:蕴藏于沉着、理性中的锐利之气——路阳访谈[J].电影艺术,2021(02):105-111.
[3] 安德烈·巴赞,崔君衍,徐昭.电影语言的演进[J].电影艺术译丛,1980(02):3-19.
[4] 徐建.《刺杀小说家》:中国电影数字化工业流程的见证与实践[J].电影艺术,2021(02):131-137.
[5] 陈旭光,李雨谏.论影游融合的想象力新美学与想象力消费[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7(01):37-47.
责任编辑:史偌霖
原文地址:http://www.whcyzzs.cn/html/2023/0313/396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