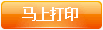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后稷网 > 文化产业网 往期 影视表演
近年来,国产电影所塑造的当代诗人形象较为充分地阐释了“诗意的式微与重建”这一主题。在部分电影中,当代诗人的光环被物质生活祛魅,镜头中充斥着非诗意的细节。但这并不代表“诗歌已死”,在另外一些电影中,诗人本人的出场较好地演绎了日常生活中的诗意,证明了重建理想主义的可能。在快速发展的时代,电影有必要运用影像的力量向观众宣传主旋律,输出“正能量”,撕掉诗人身上固有的标签,塑造极具人性光辉和鲜明个性的诗人形象,使诗人化身为理想精神的载体。
近年来,华语电影中不乏当代诗人直接出场的场景,虽然诗人并不总是作为主角现身,但其在电影中所呈现的形象却直接代表编剧与导演对当代诗人群体的理解以及对诗歌命运的关注。在相当一部分电影中,当代诗人的光环被物质生活祛魅,他们的个人理想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电影中出售诗集、朗诵诗歌等细节刻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诗意式微的证明。但编剧和导演并非意在借这些非诗意的细节来证明“诗歌已死”,而是试图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在非诗意的时代重新树立诗歌信仰。为了重建现代诗意,一些以诗歌为主题的纪录片往往邀请诗人出场,以追踪式的镜头聚焦其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在体现诗人与大众的思想感情相通的同时,也试图使诗人的形象成为理想精神的载体。
神圣光环的祛魅:非诗意细节的呈现
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时的诗人常被视为“文化英雄”,受到了广泛的追捧。但经过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转型,大众文化浪潮兴起,群众的文化需求趋于多元,诗歌越来越边缘化,其文化强势地位受到威胁。正如戴锦华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社会同心圆结构的多重裂变,已然孕含着九十年代的政治文化、消费文化,浮现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的权力裂隙;孕含着金钱作为更有力的权杖、动力和润滑剂的‘即位新神’。”[1]为了表现社会转型时期诗人的失落,很多电影往往呈现出诗人生活中非诗意的一面,甚至会赋予诗人悲剧的命运。比如刘浩执导的电影《诗人》中的李五,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因诗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众多矿工中脱颖而出,并得到领导的赏识和知名诗人张目的青睐。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李五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显得无所适从,他的诗集不再流行,他想组织诗歌竞赛,也无人理睬。更为可叹的是,他和妻子陈蕙的感情也出现了裂隙,所在的国营煤矿也被关停,一无所有的李五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外,影片还着重表现了李五的庸常,如为了名利讨好老诗人张目,怀疑妻子出轨而吃醋等。李五与陈蕙“扯毛裤”的镜头也暗示着他对两性欲望的追逐。高雅的诗歌与诗人可悲的命运、庸常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诗集”曾给李五带来梦想与荣耀,但也成为他梦想破碎的象征。因此,有人指出:“《诗人》是一曲时代的挽歌,而李五是一个丈量时代的距离的角色。”[2]
在电影《东北虎》中,“诗集”是一个具有反讽意义的象征符号。该影片可视为导演耿军所设定的“鹤岗宇宙”或“寒带电影”的代表[3],诗人“罗尔克”(其名来源于著名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居住在寒冷、萧条的小城中,痴迷诗歌几乎达到了疯癫的地步。罗尔克的朋友徐东帮其在公园门口兜售诗集,用大喇叭高喊:“本地诗人,著名诗人,诗集35元一本。”但诗集仍无人问津,卖烤地瓜的大爷用奇怪的目光注视着两人。罗尔克及其诗集的遭遇充满了荒谬性,让观众感受到某种黑色幽默,如同鹤岗这座城市的衰颓一样,居住在这个城市的诗人也失去了昔日的荣耀;鹤岗是一个非诗意的空间,罗尔克的疯癫是诗意失落的结果。
非诗意的细节还体现在一些由当代诗人自己导演的先锋电影中,如“第三代诗人”韩东导演的电影《在码头》,该片改编自韩东1998年所著的同名中篇小说。电影的叙述手法如同流水账,主要描述了以丁子为首的几位诗人与地痞、派出所民警偶然卷入了一场莫名的纷争。“码头”在电影中是一个非诗意的空间,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混杂其中,诗人们在码头抽烟、喝啤酒、调戏女服务员、与以白皮为首的地痞纠缠,在撕扯过程中诗人们的身份被降格为充满江湖气的中年男子。韩东电影中所呈现的诗人形象是“祛魅”的,更多地呈现诗人日常生活中非诗意的一面。但与《诗人》《东北虎》等电影有所不同的是,韩东对诗歌的未来并不悲观,他没有赋予影片中的诗人悲惨的命运或悲剧的结局,而是认为诗歌理想能够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延续。丁子的包裹中所藏的“东西”(诗集)是《在码头》中的象征性符号之一,它是诗人们与地痞争执的对象(在派出所打开包裹之前,白皮一直认定里面有非法物品),而它的“金光闪闪”,又暗示着它承载了丁子等人的诗歌理想。
20世纪80年代早已远去,笼罩在诗人头上的神圣光环早已黯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导演与编剧,多少会怀念曾经的理想主义氛围。但缅怀过去,不代表只能在电影中呈现诗意的式微与诗人的失意,导演与编剧完全可以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重新寻找诗意,呈现有血有肉的诗人形象。
日常生活的突显:诗人的本色出演
以当代诗人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纪录片追求真实、贴近生活的效果。诗人杨碧薇认为这类纪录片是“中立的、日常的,以纪实美学为依托,其大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领域日渐蓬勃的审美日常化”[4]。诗人若健在,通常会直接出现在纪录片的镜头中,家人、朋友、同事等诗人的近距离接触者,也会在电影中发声。蒋志的作品《食指》是近年来较早的一部当代诗人纪录片,虽然影片时间较短(45分钟),拍摄、剪辑的画面也有些粗糙,但这是第一次以影像的方式展现诗人食指的人生轨迹及其因精神疾病住进福利院的生活状况,中间还穿插了一段根据食指的诗歌改编的同名戏剧《疯狗》。在当代诗歌史中,食指常被认为是“朦胧诗鼻祖”,由于种种原因,食指长期被排斥在中国当代诗歌史、文学史的范畴之外,致使其被湮没。直到1994年《诗探索》编辑部举行了“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活动后,食指的生平与创作才逐渐为读者所知晓,并在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了一波“食指热”,纪录片《食指》便是“食指热”的跨界反响。《食指》之后,越来越多当代诗人的生平事迹被拍摄成影像,如刘宽导演的《日常的奇迹》记录了诗人黄灿然的日常生活,陈捷导演的《我的师尊木心先生》得到已逝诗人木心的弟子陈丹青的鼎力支持,呈现了诗人木心传奇的一生。吕美静导演的《流亡的故城》尤其值得一提,该片在顾城逝世二十周年之际上映,以亲友回忆的方式呈现了诗人顾城幼时至其辞世的生平事迹,其父顾工、相关人物李英、诗人西川与杨炼、诗歌评论家唐晓渡等人都在片中有大量镜头。该片试图拨开层层云雾,将顾城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人”,并以顾城的生平与创作为线索,使观众了解到曾经的“诗歌热”,在某种程度上,该影片是对20世纪80年代的怀缅。
上述提到的诗人,如食指、顾城等,他们进入纪录片导演视野的时候都已是进入诗歌史的诗人,而对于“草根诗人”或“打工诗人”,许多观众则是透过电影第一次了解他们的生活。秦晓宇《我的诗篇》和范俭《摇摇晃晃的人间》是两部表现“底层写作”的典型作品,前者以陈年喜、邬霞、乌鸟鸟、老井、吉克阿优、许立志等“打工诗人”的日常生活与创作为素材,并邀请诗人们出镜。观众从电影中能看到诗人们在工厂、矿井等场所辛勤工作的场景,也能看到他们在工作之余进行写作的场景,展现了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我的诗篇》是诗歌与传媒的完美结合,它让更多观众知道了“打工诗人”这一群体的存在,并对他们的命运产生共鸣,“打工诗人”也借这部电影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调整了个人的生活状态,其作品也拥有了更多的读者。更重要的是,《我的诗篇》引发了全社会对当下工人命运的关注,从而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意义。
范俭《摇摇晃晃的人间》是以跟踪式的镜头表现草根出身且身有残疾的女诗人余秀华的生活与情感经历。2014年,余秀华因《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一诗在网络爆红,此后关于她的争议一直不断,《摇摇晃晃的人间》从某种程度上也增加了余秀华及其诗歌的热度。影片的主要线索之一是余秀华的婚姻问题,在影片中,余秀华自诉与前夫完全是奉父母之命而成的婚姻,影片也多次表现余秀华与前夫的情感及生活矛盾。余秀华喜欢用电脑进行写作,而其前夫只是个老实巴交的建筑工人,不懂诗歌,也不理解余秀华的精神世界。两人的隔阂越来越大,影片的结尾,余秀华选择了离婚。影片的另一条线索是余秀华的成名过程,她多次朗诵自己的诗歌,并出席诗歌研讨会,回答读者的提问。值得注意的是,余秀华的婚姻问题与成名过程是纠缠在一起的,甚至有观众怀疑《摇摇晃晃的人间》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余秀华婚姻的解体。但无论如何,《摇摇晃晃的人间》使余秀华的诗人形象深入人心,这部电影与《我的诗篇》都可视为近年来“底层诗人”本色出演的代表作。有人给予了这部影片高度的评价:“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在人物塑造、叙事表达以及构图节奏上都有着较高的成就,代表了一代中国纪录片人创作水平的高度。”[5]
诗人本色出演,向观众呈现出日常生活中潜藏的诗意。尤其是“底层诗人”的现身,更让观众感受到平凡的人生也能实现理想。其实,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电影与诗歌一样,都发挥着弘扬社会正能量、重建理想主义的精神功能。电影中所塑造的诗人形象,也应该拒绝刻板的标签,体现人性的光辉。
重建理想的努力:人性光辉的闪耀
近年来,在许多国产电影中,诗人形象总是被边缘化,被贴上郁郁不得志、甚至“疯癫”的标签,如陈丽英导演的作品《顾城别恋》中饰演顾城的演员的夸张式出演,又如《像鸡毛一样飞》中江郎才尽的落魄诗人欧阳云飞逃离城市后遭遇了一连串荒唐离奇的事件、“下海”办养鸡场的诗人陈小阳,再如《东北虎》中精神失常的诗人罗尔克。事实上,活跃于当代文坛的诗人,并非被生活压榨得一无所有,也没有那么多精神失常的现象,贫穷、疯癫、神经质不应该成为对诗人的刻板印象。电影对诗人形象的塑造固然要结合时代语境,但更重要的是符合实际,发掘其人性的光辉。
导演徐红的《梅里雪山》以诗人马骅的真实事迹为素材,讲述了马骅自愿来到云南梅里雪山脚下的小村庄,在当地乡村小学义务支教的故事。在片中,马骅用自己的存款与稿费为乡村小学修建了篮球场和澡堂,向孩子们传授知识,宣传环保思想。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一次车祸中,马骅坠入澜沧江,将自己的青春年华永远留在梅里雪山。影片中马骅的崇高品德、诗歌理想与梅里雪山的圣洁相交融,使诗人的形象更具光辉。在现实中,马骅逝世后,其友人将其诗歌整理成《雪山短歌》出版,其诗作正好与电影中所讲述的马骅的事迹相呼应。《我的诗篇》中对“打工诗人”形象的塑造也颇为成功,陈年喜等诗人都来自农村,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始终心存对诗歌理想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放弃过诗歌写作。比如邬霞是一名在制衣厂打工的女诗人,她每天都在流水线上忙碌,制作一件件吊带裙销往全国各地。在片中,邬霞朗诵了自己的诗作《吊带裙》,该诗寄寓了她对穿上吊带裙的“陌生的姑娘”的美好祝愿。因为工作原因,邬霞很少有机会穿上自己亲手制作的吊带裙,但她却希望每一个穿上吊带裙的姑娘都能拥有幸福的生活,这样的祝福非常打动人心,可以说,邬霞的诗歌是有温度的作品。
略有遗憾的是,近年来的国产电影中,像《梅里雪山》《我的诗篇》等表现诗人正面形象、充满积极价值观的作品并不多,对诗人形象的塑造还有待进一步探索。田波执导的《柳青》在一定程度上为诗人形象的呈现提供了典范。影片着重表现了柳青放弃北京的优渥生活、扎根山西皇甫村,与当地农民一起进行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建设的事迹,以及柳青创作《创业史》这部史诗性著作的过程。片中的柳青无疑是一个坚定理想信念的人物,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文学事业和社会主义农村建设。更引人关注的是,影片将柳青的形象置于时代的背景下,勾勒出作家的个人生命与大时代之间的关系,并突出了柳青的理想精神对当代作家的影响。曾有这样一番评论:“《柳青》可说是在‘中国性’审美关照下,一次对诗意叙事、诗意审美的叩访。”[6]《柳青》对今后影片中诗人形象的塑造有较大启示。
新世纪已经进入第二个十年,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国产电影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期。身处大时代,导演和编剧应该进一步明确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撕掉诗人身上的刻板标签,在电影中更为深入地塑造具有鲜明个性与“正能量”的诗人形象,挖掘日常生活中所蕴藏的诗意,使国产电影充满理想主义的光辉,实现电影与诗歌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2]张韵.《诗人》的时代表征与两性情感刻画[J].电影文学,2021(20):119-121.
[3]耿军,石文学.虚构的“鹤岗国”,现实的舆论场——电影《东北虎》导演耿军访谈[J].电影新作,2022(01):31-38.
[4]杨碧薇.日常性与传奇性之间的摇摆——华语电影中的诗人形象[J].南方文坛,2021(04):176-179+190.
[5]张静.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的人性关怀与诗性追求[J].电影评介,2017(14):35-37.
[6]徐开玉.《柳青》:诗意叙事、写意影像与平民英雄书写的新维度[J].电影评介,2021(17):42-46.
责任编辑:史偌霖
原文地址:http://www.whcyzzs.cn/html/2023/0116/392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