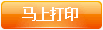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后稷网 > 文化产业网 往期 影视表演
纪录片既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又有文化层面特有的生命力。人文纪录片《人生第二次》用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将微观的人物境遇照进宏观的社会现实,塑造了当下和未来。纪录片是一种呈现真实生活、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的艺术形式。随着纪录片创作方式和创作类型的多元化,新媒体传播的手段愈发多样化,当下,人文纪录片的创作已经成为纪录片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人文纪录片《人生第二次》通过《圆》与《缺》、《纳》与《拒》、《是》与《非》、《破》与《立》四组两两对立思辨、八个感人真挚的故事,坚持“真人、真事、真情感”的拍摄手法,讲述了当今社会发展中真实存在的个体境遇,直面人心冷暖。在大众传播语境下,兼顾纪录片的社会性、思辨性、审美性,对纪录片创作的理念进行了创新与融合,呈现了耳目一新的记录形态。凭借多视角叙事艺术的建构、故事化的哲理思辨、直面真实与生命叙事的纪实理念,讲述中国人身边的故事,在本体传播上取得理想效果。
影像表达:多视角建构叙事艺术
叙事是话语表达的重要形式,在具象事件的陈述中,叙述者是故事的传播源。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读者或观众的审美经验来源于具体作品中讲述者的现身说法,不同的叙述角度形成了不同的叙事视点。“视点是身体所处,或意识形态方位,或实际生活定位点,基于它,叙事性事件得以立足。视点并不意味着表达,而仅意味着表达基于何种角度而展开。”[1]法国文学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提出,不同的叙事视点可以形成不同类型的叙事焦点。主要有三种:第一,没有聚焦或者零聚焦的叙事,叙述者此时处于“全知状态”,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第二,有固定的内聚焦,说明陈述的事件或故事是经过唯一一个人物直觉的过滤,焦点随着进展的变化而形成变化的内聚焦,焦点随讲述者变化而形成多重的内聚焦;第三,外聚焦的叙事,读者和观众无法直接走进人物内心世界,只能依靠叙述者存在。由此可见,聚焦主要是体现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认知关系,叙事者可以是作品中的“我”,也可以是非参与人物的“他”。
在人文纪录片《人生第二次》中,导演在复调循环的叙事语境中,运用多角度叙事的手法。在第一篇章《圆》中,卫书银、占绪莲夫妇寻找被拐儿子的视点、儿子卫卓在生父母与养父母之间抉择的视点、警方为解救被拐儿童所作努力的视点。从这三种不同的视点,对被拐这一事件进行解析,一层一层地靠近所要讲述的事件,并且也在历时性和共事性的时空解构中,达到叙事的视阈扩展。《拒》篇章,在全知视角讲述的故事中,通过民营医美机构负责人、追求医美“快餐”的消费者、公立医院整形美容科医生、因脸部膨大寻医的冯婷等多重视角来讲述医疗美容行业与消费者之间道不清的关系,留给观众思考现代医美意义的空间。叙事视角的灵活也促成了对真实人物形象的塑造,无论是扁平人物还是圆形人物,都形成了对纪录片本身叙事视角的建构。《纳》中乐观幽默、坚强不屈、勇敢自立、慢慢接纳轮椅、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何华杰,在“希望之家”自学复健、学坐轮椅、考取残疾人驾照、自驾川藏线、增加训练量,离开妈妈的庇护一路蜕变,通过这一系列具体的全知视角,人物得以塑造出来,同时也刻画出一位在何华杰背后无私陪伴支持的伟大的母亲邱娟妹的形象;《破》篇章则是通过女性视角,审视当下社会中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系。
叙事视角作为重要的叙事技巧,在故事讲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人文纪录片《人生第二次》中,叙事视角的转换,给观众带来不同的观感和思考,也使每个故事呈现出不同的艺术效果。无论是拍摄时选取的视角,抑或是后期剪辑过程中的视线思考,不同的视角可以将碎片化的生活细节重组,通过视角的变化,大大拓宽创作者的切入角度,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观感,也给纪录片本身带来了更多解读意义。
文本与视听:故事化的哲理思辨
纪录片的创作经常面对难以解释而又必须解释的故事命题,轰轰烈烈的戏剧冲突和可歌可泣的人物故事固然让人动情,但是不动声色、细水长流的情感思考更值得人回味、咀嚼和共鸣。从电影被发明出来的那一刻开始,关于电影“故事——记录”的纷争,从卢米埃尔与梅里爱,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与现代电影的分庭抗礼,再到巴赞“纪实美学”,关于“纪实”理论的阐述就没有停止过。纪录片从来就没有失去故事性,它本身就有故事片的属性。“无论纪录片还是故事片,其实都是在讲故事。”[2]故事文本的讲述,需要矛盾与冲突的构建,主题与主题的碰撞。在人文纪录片《人生第二次》中,导演用故事片的思维方式解构了纪录片的创作,在每一个故事中,都能看到有细节有情节有情感,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尾。《圆》讲述了被拐儿童重新回归家庭;《缺》讲述了缺失家庭之爱的孩子在另一方天地感受到温暖;《纳》讲述了双腿瘫痪的年轻人脱离母亲庇护征服川藏线;《拒》关照了整形美容产业下发生的故事;《是》聚焦法治体系下社会的公平正义、法治与人情;《非》关注了出狱后迎来新生的人如何处理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破》聚焦三对婚姻关系破裂的家庭,通过对待孩子、家庭、婚姻关系的态度,反映当下社会真实存在的问题;《立》所关注的是来深建设者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该纪录片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人如何处理与人的关系、人如何处理与社会的关系。整体的主题内容和每个篇章的命题都有一种哲学思辨意味,让纪录片更具哲思和艺术性,实现真实自然的“有意味的形式”。
在圆与缺、纳与拒、是与非、破与立之间,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和辩证思维支撑起创作者真挚的情感想象和影像表达。当文本与视听达到协调时,纪录片才会达到客观与主观、真实与纪录、审美与艺术的统一。在视听方面,导演运用影视创作中蒙太奇的手法处理故事冲突,在《缺》篇章,小金子回到爷爷家,给奶奶烧纸之后,是母牛哺乳两只小牛的镜头,舐犊之情,人何以堪!主题——并置的镜头创造出原本单独镜头所不具备的含义——控诉了丢下孩子的父母,这一幕亦对观众形成冲击,进而引发其思考。在《纳》中,何华杰和“希望之家”的病友们征服川藏线,他能否离开妈妈的庇护自理?是否能重新寻找自我,超越自我?在发现矛盾与解决矛盾的过程中,长镜头展示了何华杰在冰雹大雨中完成了独自坐轮椅的仪式,完成了他的“人生第二次”,喜极而泣。在完成雨中轮椅的仪式之后,川藏线上架起了彩虹,用蒙太奇的镜头语言寓意风雨之后的新生。《立》篇章中,黄妹芳为了让孩子上初中而努力生活,穿梭在生产流水线和繁华都市中,背景音是时钟的滴答声和加速的钢琴声,像是上紧的机械发条,又像是时间的流逝,下班之后,充满生活气息的背景音又回来了。黄妹芳读朱自清的《匆匆》,细腻地刻画了时间流逝的踪迹,彰显了纪录片创作者对柴米油盐中诗意的歌颂。
纪实观念:直面现实的生命叙事
电影与生俱来就有一种特殊的捕捉自然与生活的能力。谈到关于电影的观念,安德烈·巴赞指出:“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电影就是要让人去思考影像的价值与深度,这需要理论和实践共同表述完成。影像作品的呈现与客观现实中的被摄物的统一,也就是对现实的完全复原,这要求纪录片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具有客观真实性。“真实性在纪录片里要包括五个方面:空间、时间、人物、事件和细节。这五个真字是纪录片存在的基础。可见,真实是纪录片的首要品格。因此,纪录片不能虚构、扮演、重现。纪实性,对于纪录片是具有质的规定性之品格。”[3]纪录片的观念和价值在于直面真实发生的社会现实,又不完全复原现实的妥协和让步,所以它需要在接近生活和体现生活的同时,在纪实性和真实性之间达到平衡。
早在20世纪20年代,弗拉哈迪就运用简单的摄影记录方式,传达了镜头下遥远世界的真实诗意的生活气息和勃勃生机;出于对社会生存发展的关心,格里尔逊认为纪录片要“对真实事物做创造性处理”;以理查德·利科克为代表的美国“直接电影”要求纪录片在“不介入的长期观察与拍摄中捕捉真实”;法国“真实电影”的创作者们则认为“要获得事物深层的真实,拍摄者必须主动参与到事件的进程和环境中去”。事实上,随着纪录片的发展,纪录片的创作观念越来越多元化,受众范围也逐渐扩大化,不再是“一群精英拍给另一群精英看的奢侈品”,对“真实性”也有了更深层次的解读。在纪录片《人生第二次》中,并非每件事情都是可具体深入地用镜头直接描述的。面对自己的拍摄对象,导演组采用“蹲拍”和“跟拍”的方式,以“墙上的苍蝇”式记录拍摄对象的日常生活和细节,着重跟踪记录事件发展的过程,在过程中保持自然客观,展示真实环境、真实人物、真实时间、真实空间,将真实世界的细节汇成故事主题。
“一个有良知的纪录片人,在采集素材的时候,都会很尊重生活的原貌,进行谨慎的记录,因为这是在记录历史。这是第一个层面的诉求。第二个层面,纪录片作为一个作品,其制作自然不可能停留在只是呈现或罗列生活场景或事件过程的阶段,而是要用这些素材来表达一个观念,或实现一个主题。”[4]伟大的主题往往蕴含在平凡的生活中,个体微观的叙事对象,可以拓宽主题的深度与广度,提升故事的可信度、真实性,将微观记忆中的个体性,延展到宏观群像中的社会性。人文纪录片《人生第二次》通过还原生活和浓缩生活的结构,表现出一个又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侧面,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八个故事中,可以看到真实的当代中国人的个体形象与社会群像。其通过影像向观众传达了情感、价值判断、人生思考、人生的维度,一个个平凡但又不普通的人在逆境中与命运抗争、和解,展现出中华儿女骨子里的不屈和韧性。《缺》关注了“梦想之家”中的“老爸”柏剑以公益的方式关爱处在“被爱遗忘”困境中的儿童,在26年里收养120多个儿女的感人故事。这些孩子身上有着相似的印记:由于父母离异或家庭不和睦,他们在受教育的同时,进行体育训练,并借此改变命运。在《拒》篇章中,讲述了随着社会发展,整形美容产业中发生的故事,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到“我的身体我做主”,对整容的争论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议题。导演没有回避观念上的议论纷争,将每个人物对医美所持的态度不加修饰、不加干预地通过讲述和对话的方式展示出来。
人文关怀:讲述中国故事
“纪录片拥有其他形态影视作品无法取代的独特魅力,拥有认知世界和自我的强大功能,是富有启发性的艺术,是富有文化内涵的艺术。”[5]近年来,中国纪录片的创作逐渐转向人本身。从《大国崛起》《敦煌》等探索中华五千年文化底蕴、展示主流话语的历史人文关怀,逐步转向《人间世》《四个春天》《人生第一次》《人生第二次》等关注人和社会冷暖的社会人文主题纪录片创作。可以看出,创作的纬度不断延伸扩展,创作方式不断更迭变化,拍摄手段和技术也日新月异,叙事策略也在不断演进。人文纪录片《人生第二次》,利用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将微观的人物境遇照进宏观的社会现实,塑造着已知的当下和值得探索的未来,对社会中人们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空间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与剖析,每一个故事都犹如一面镜子映照社会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纪录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艺创作方式,担负着“解释历史,阐明抉择,增进人类之间的互相理解”的使命,它可以用短小精悍的篇幅,拓宽中华文化的广度和深度。
在人文纪录片《人生第二次》中,每一个小家的背后都是大家的力量。走出家庭,进入社会,他们的身份是父母、子女、丈夫、妻子,也是被拐的儿童、残疾人、追求美的整容者、刑满释放者、主播、来深打工者、法官,等等。从这些人物身上,能看到他们与过去告别、开启新生活、进入新领域的决心。卫卓的“人生第二次”是回到真正的家,与父母、哥哥写下“团圆餐馆”,开始新的生活;“梦想之家”的孩子们,他们的“人生第二次”是再次被社会关爱;何华杰的“人生第二次”是接纳自己,学着在轮椅上独立生活;为弟弟“讨公道”的哥哥刘占江,虽然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是回到了正常的生活轨道,陪伴和照顾家人,带着整个家庭面对第二次生活;出狱后的毛徽,面对家庭和等待自己的女朋友,开始他的“人生第二次”;“来深建设者”黄妹芳重新学习技能本领,迎接新的人生。他们体现了当今中国社会中生命个体真实的生存状态,琐碎的生活、情感关系的起伏变化、梦想破碎后的坚韧不屈都反映出了当下普通中国人最真实的精神力量。时代需要艺术工作者主动扛起文化担当,履行使命。《人生第二次》的创作者利用手中的摄影机,素描平凡中的动人景象,洞悉时代变化之迅速,呈现了当代社会文化的丰富性,用摄影机描绘身边的动人色彩,诠释了当下中国的时代精神,讲述了“中国故事”。
参考文献
[1]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M].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单万里.代序:纪录片与故事片优势互补[M]//希拉·柯伦·伯纳德.纪录片也要讲故事[M].孙红云,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33.
[3]任远,彭国利.世界纪录片史略[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4]何苏六.纪录片的责任与影响力[J].现代传播,2005(01):83-86.
[5]单万里.纪录与虚构(代序)[M]//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7.
责任编辑:史偌霖
原文地址:http://www.whcyzzs.cn/html/2023/0114/391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