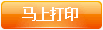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后稷网 > 文化产业网 往期 影视表演
第75届戛纳电影节再度以海报形式致敬电影《楚门的世界》,唤起了公众对信息环境的重新思考。与传统观影模式下观众坐在电影院的黑暗环境中,身体的静止与意识高度活跃并行不同,流媒体平台的观众在更易接触电影的同时也更易受到干扰,导致感知弱化,同时意识的缺位也造成了参与的丧失。然而,数字技术在加速后电影时代到来的同时,也孕育了电影未来新的可能。相较于电影院以隔断为形式铸造的特殊空间,互动电影更倾向于探索更具包容性的“主动降噪”,同时为感知的重铸提供物质基础和理论准备。
数字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人类迈向数字化生存的脚步,在社会运转线下向线上的转型中,信息环境需要被重新定义。后电影时代的到来,在此发生的不仅是观影空间或媒介上的转变,更是影响到电影作为生命体验在本体论层面的关键性转折。
被展现的现实与认知重构
官方海报将主人公楚门(Truman)自摄影棚的拟真环境边缘拾级而上的图景作为原型,这是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的最后一幕,也是他离开摄影棚成为真正的人(true man)前最后的路径。电影节组委会将其背后的话语阐释为“柏拉图洞穴隐喻的现代再现”,并希望借此唤起人们对现实与被展现的现实之间界限的思考。再度激发人们在数字时代对信息环境的重思,引发人们对感知的批判性解读。
信息的真实性一直是数字时代的热点话题,当目光被聚焦于影像时,著名的《电影语言的演进》可以被看作对数字时代的现实与真实、现实与被展现的现实的探讨和启发。巴赞在文中指出了20世纪20至40年代两类导演关于影像看法的分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认为,相较于原始的影像,蒙太奇赋予电影以“新的东西”,另一部分人则将影像更多地看作对真相或现实的揭示。新的基础技术语言召唤着信息认知范式的更新,数字影像本身的真实性之辩与影像主观性的探讨在今天成为一个整体。每个人都可能是今天的“楚门”,在探讨图景真实性的“戛纳问题”背后,个体对真实概念的认知和对数字化生存的态度同样值得注意。伴随着数字技术推动下新的“景观化”和“屏幕时代”的到来,真实与虚假的二元对立关系面对数字影像的超真实表现产生了松动。
楚门离开摄影棚的必要前提是他意识到自己周遭虚假景观的存在,也从侧面暗示着数字化生存中公众对信息环境与拟态环境的辨析。认知框架的打破先于他的实际行为,催化了他的最终决定。诚然,构成人类社会根本运行逻辑的基础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超越社会生产力发展现状的认识既难以被确凿的印证,又缺乏实践的物质基础和足以为其提供支撑的技术语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认知观念的重思和思维框架的破除只能在技术革新的背景下发生。影片中楚门重建自己对“真实”的认知,现实生活中封塔纳用刀片划开画布,不论是艺术作品中对真实生活的追求,还是现实生活中艺术品的创作,技术的进步从来都不是打破认知框架的唯一选择,相反,对技术的重思才能让我们在未来到来之前,在贝尔纳·斯蒂格勒口中的“两次重叠”发生之际,不因对技术发展方向的误认而扼杀希望的幼苗。
幽灵性场域与环境感知
观众习惯于同电影达成一种共识,他们会对屏幕上的显像以及背后的电影世界产生有限的无条件信任。这意味着在特定的观影时间内,他们不仅接受一切电影情节的生成和推进,而且愿意毫无保留地将感知投入镜头和蒙太奇建构而成的电影时空中。他们娴熟的适应镜头,借助银幕在电影世界的空间中穿行。在时间层面,他们不仅适应了被蒙太奇重叠的时间,将自己的时间与作为客体对象的电影时间相重叠,更打破了时间在现实世界惯常认知中的线性特点,在画面的带领下穿梭于时间流中。看似是房间、座席、放映机和银幕简单组合的电影院却具备自身的特殊含义,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电影发生的时空装置,3D技术、环绕声、高帧速播放等具体技术在特殊环境得到更好的展示,观众更深层次情感的感知或电影之“思”也在特定条件下更为常见,这意味着观影的环境不仅影响着观众表层的观影体验,更涉及个体在幽灵性场域中的生命体验。
电影的意义存在于银幕所展现的另一个世界中,同时也通过银幕向现实溢出,向观众静坐的放映厅蔓延,与之相遇、为之捕捉,进而使观众得到感知与解读。观众以幽灵而非主体身份将自身置于电影世界,幽灵性场域中的存在缺乏确证性,肉身周遭的黑暗环境也无法被感知,但这种环境却成为电影体验的一个装置性准备。环境本身是一个介质,也是允许意义进入的前设条件。周边的一片漆黑推动座席上的观众更彻底地将意识投入电影,让他们的意向行为受到更少的干扰。观众周遭的黑暗意味着“空无”(Void),他们的眼前只有银幕,这恰恰说明观众周围的黑暗是概念上不存在但却具有其自身意义的。
在漆黑的电影院里,我们看到了什么?银幕大概是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因为在电影院的封闭空间中,只有银幕是“被允许”昭示自身存在的——观众被要求固定在自己的座席上,不应移动也不准发出声音,他们即使直视周围的漆黑也无法获得任何信息。现象学的重要概念“视域”(Horizon)强调源于主体流动的视点,其意向对象(Intentionaler Gegenstand)会呈现出差异化的样态。视域概念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来自视线的意义话语权,无法被视线照亮进而得到不具备存在意义的感知信息。如此看来,观众的视线和感知实质上对银幕和黑暗场域进行了区别,电影院这个方盒子的六面体内部似乎只有一个平面具有意义,观众所处的环境仿佛变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难道这个观影的特定场域不具备自身的意义吗?立足于后电影时代,把流媒体平台的观影体验作为对照系,作为观影特定环境的电影院才显得尤为重要,从苏珊·桑塔格到大卫·林奇,一批优秀的电影人旗帜鲜明地捍卫电影院对电影的特殊意义。银幕作为电影院内观众感知中唯一的“存在者”,并不仅是投射视线的“窗口”或意识沟通的“桥梁”,更像是容纳观众从现实世界,从黑暗的影院穿行于电影世界且自身置入其中的“虫洞”,也是观众获得电影体验的来源。
从建筑环境的视角来看,四面围合的建筑会让身处其中的人产生逼仄之感,但为何电影院一反常态,赋予了观众以“通透”之感呢?银幕正是这种体验的来源。理想状态下的电影观看过程往往是观众完全沉浸于电影世界中,忘我的投入到眼前的银幕所显示出的世界内的状态,“自身置入”的效果在此刻成为现实。这种状态下除作为意向对象的电影外,主体所处的环境似乎并不存在,甚至观众同银幕之间的距离也被忽略,黑暗不仅隔绝了观众与电影院外的世界,也为银幕中展现的、独立于外部世界的电影世界提供了生成和运行的环境前提。
在时间的重叠与空间的挤压中,观众获得了另一个维度的生命体验,他们“进入黑暗的影院并放弃行动的能力,不是入梦,而是从现实中醒来”。传统的放映厅内,环境相较电影本身是不存在的,其意义在于通过自身的隐去,让不可见环境下的电影获得更大的激发,电影依托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场域而具有迷影(Cinephilia)的强大魔力。在同外部世界相隔断的观影进程中,个体看似在被动地接受信息,但被封闭的环境和可以不断延伸的意识空间催化了观众感知的向前展开和意识更高维度的活跃。观众在放映厅内高敏感度的意识活动带来了一种象征着行动的特殊状态,是短暂地从柏拉图三种灵魂运动类型中的感觉灵魂向能意灵魂过渡的源头。也正是在电影院中,意识的参与和延展使人尽可能地保持在能意层面,不至于后撤成为感觉灵魂,这也意味着电影院中观众的参与让他们不仅观看表象的影像,也调动自己的诸种官能以得到感知,得到深层次的生命体验。
参与的丧失与感知的重铸
在社会运行逐步恢复常态并迈向发展新常态的今天,观影体验中曾因参与的丧失而带来的被阉割的电影体验让从业者和研究者开始思考,在流媒体及其背后超工业的力比多经济笼罩下,参与的丧失是否真实而不可逆。
电影《囧妈》将公映从院线转向网络流媒体平台曾激起讨论的热潮。流媒体平台的电影和电视剧的区别在哪里?抛开时长、节奏等因素不谈,今天一部分专为流媒体平台打造的“力比多电影”只顾短期经济效益而充满低级趣味,似乎除了在平台上被划归“电影”一类外,更像是和电影时长相仿的视频影像。短视频化或电视剧式的“电影”有时以电影之名,将机械刻板的精神刺激和冗余烦闷的“垃圾时间”安置于千篇一律的叙事流水线上,观众只能从中获得感官刺激或精神的麻醉,这样的影像作品自然毫无“电影体验”可言。或许流媒体平台的确如同我们想象的那样,让观影的门槛变得更低,为每一个观影者带来更便捷的观看电影的权利,观众可以自行调整播放速率,操作进度条,暂停又复播,面对触手可及的文化产品,公众接触电影所需投入的精力和情感成本变得低廉,也在指尖的滑动中逐渐远离曾经从电影中可获取的生命体验。
现实世界中自然流逝的线性时间在电影院内仅以影片时长的形式显现,传统的空间关系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同电影世界相融,如若独立的观影时空不复存在,外界传来的光亮和声响不仅在客观上会为观影体验带来负面影响,观众的感知过程也容易受到干扰,延伸向生命体验的观影之时空感知也极易遭到破坏。外界的冗余信息相对于电影是一种感知与解读的“噪音”,电影院作为隔绝外部环境,让观众与外界达成一种分离状态的装置,是面对噪声的抵抗与防御,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分隔为手段的“被动降噪”。声学领域的有源消声技术(Active Noise Control, ANC)指在识别外界噪声的基础上,对其施加额外的反相声,利用声波的相消性干涉,让振幅相等且相位相反的初级声源和次级生源相互抵消,在特定环境下消除噪声,在被动降噪基础上施加后天人为加工达成的“主动降噪”。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影游融合”“VR电影”等电影形式的探索不断为电影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可能,在人机自由交互的美好想象中,观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通过交互行为以具备主体性的形式存在于电影世界中,这为参与的复归和感知的重铸提供了开放的通路。将外界同电影世界相冲突,无法被隔离在观影体验之外的信息以新的方式纳入完整的电影体验中,以同电影体验相似的感知与信息获取模式,对外界的信息进行处理,不是倾尽全力将其隔离,而是让外界的信息融入整体的电影体验之中。在广义层面,将电影体验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既是电影体验扩容的可能路径,也是面对感知干扰时的一种“主动降噪”的尝试。
梅洛·庞蒂提出人的信息感知渠道不仅局限于视觉,还包括触觉、听觉、嗅觉、味觉、动觉等知觉方式。以具有明确主体意识的电子游戏为参考,观众身体进一步的调动在互动电影的畅想中被认为具备实现的可能。用户置入影像世界并处于幽灵场域的特定环境中,“在心灵—身体—自然的三位一体中,身体是沟通心灵与自然的中介”,作为用户与电影世界的桥梁存在,强化了用户与环境的沟通。
斯蒂格勒认为,不论是电影院还是流媒体平台,观众都可以通过观看,而不需要进行其他举动——从作为第三持存的电影中摄取新的、即成性的记忆,从德勒兹笔下晶体形式的时间中获得能量远大于现实生活的生命体验。今天越来越少的流媒体平台观众将自己的意识“附着在这段流动的时间上”,他们观看的对象更多地集中于影像本身。媒介的切换丧失的不仅是参与,更是空间和时间的体验。但互动电影在这一点上似乎同“电影”不同,相较于传统观影模式中的“观众”,互动电影的体验主体更是以“用户”的角色存在,在主体意识的充分调动中接近参与的复归和感知的重铸。
正在走出摄影棚的楚门面对着一个对他而言不确定的未来,我们也面对着数字技术展示的多样未来、元宇宙等概念。海德格尔“艺术成了体验(Erleben)的对象,而且艺术被视为人类生命的表达”强调了艺术是被以美学的、体验的方式认知的,并且被指涉为一种意义上人类自身的展开,但后人类纪的诸种艺术形式似乎追逐着海氏字面上的能指。艺术感知和体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沉浸式体验”作为热门话题和宣传标语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克服对技术与未来的盲目乐观,将目标铆定于感官刺激背后的精神通达。无论是电影院中的观影体验、流媒体平台上的视频浏览,还是互动电影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探索,最重要的是电影背后我们产生的思索和生命体验,也是透过形式之迷雾探寻电影之“思”,从而重拾面对不确定未来的信念。
参考文献
[1]余慧元.“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J].学术月刊,2005(11):30-36.
[2]吴冠军.作为死亡驱力的爱——精神分析与电影艺术之亲缘性[J].文艺研究,2017(05):97-108.
[3]贝尔纳·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2:感性的灾难[M].刘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
[4]徐永成,温熙森,陈循,等.有源消声技术与应用述评[J].国防科技大学学报,2001(02):119-124.
[5]黄铭.怀特海机体哲学的环境思想及其实践意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30(09):105-109.
[6]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M].方尔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7]海德格尔.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林中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责任编辑:史偌霖
原文地址:http://www.whcyzzs.cn/html/2022/0829/381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