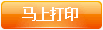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后稷网 > 村委主任网 民俗非遗
晋北一代,黄土高原,几千年之前就盛产黍米。糕,便是黍米面食之精品。这方水土如何滋养这一方人呢?这糕凭着它耐寒、高热的特质,必然是首当其冲、无可替代之物。所谓三十里莜面四十里糕,十里的荞面饿断腰,说的就是糕可以给予人的正能量,远非其它美味佳肴可比。
鸡蛋碰糕与糕花子
□任勇
某天在某饭店,鄙人偶遇一大同名吃,名曰鸡蛋碰糕。听起来颇有趣味,而实际上就是把煮熟的鸡蛋搞成碎块与素糕拌在一起,操作流程极其简单,但吃起来的确很香。因为鸡蛋也好,炖肉也好,天生就是黄糕的绝配。如此的鸡蛋碰糕,随了吃客的胃口,却混淆了它本来的意思。
鸡蛋碰糕,鸡蛋与糕无须多言,讲究的是那个碰字。当初老百姓说的鸡蛋碰糕,是吃不起鸡蛋蘸糕,只能用糕往鸡蛋上轻轻一碰,算是沾了一点荤腥。换句话说,鸡蛋碰糕是穷汉吃糕,是极为寒酸的一种自嘲。与鸡蛋碰糕可以“媲美”的说法,还有猪尾巴抽糕,羊蹄踢糕云云。顾名思义,用一条小小的猪尾巴往糕上啪啪一抽,用本来就没有几丝肉的羊蹄往糕上一踢,这就算见了荤,吃吧,甩开腮帮子吃吧。这些民间说笑之词,或确有其事,或只是村子里面大树之下的“幽默大师”信口一说,大家伙儿哄堂一笑而已。想想那个年月,日子过得紧巴,吃不饱穿不暖太正常不过了,能够吃上一顿糕就蛮不错了,哪还有炖肉、炒鸡蛋那么高的奢求。我有一老友,出生在助马堡长城脚下,他讲过一个故事,让人们听后笑得前仰后合,大笑之后却心情难以平静,甚至略感沉重。说他们小时候在乡里一所旧庙改成的学校里读书,学校里只有二十几个学生,一二年级、三四年级的都有,老师呢一老一少有两个。那位年长的老师姓范,擅长讲语文课,尤其是讲文言文和古诗词,读起课文来抑扬顿挫摇头晃脑,特有老文人的风范。他的学生里有一位是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儿子,这位公社干部知道范老师乃穷书生一枚,生活一定拮据,便让他儿子带几颗煮鸡蛋慰劳范老师,遭到范老师一口拒绝。范老师对学生讲,老师的日子过得好,每天黄糕炖肉,不缺不缺。学生们看着老师补丁摞补丁的衣衫,摇头不信。第二天早上,范老师走进教室,学生们一眼看到老师的嘴巴满满的油腥,便问咋回事?老师一笑说黄糕炖肉是也。以后几天早上,范老师与学生们见面,都是满嘴巴的油腻,同样以“黄糕炖肉是也”答复大家,惹得学生们直咽口水。那位革委会主任的儿子才信以为真,认为父亲对老师的关照纯属多余。不知过了多久,有学生爆料,说范老师哪里是吃了黄糕炖肉,他无非是在屠宰坊那里讨得一小块猪皮,每天离开家时往嘴巴上抹了又抹而已。
文人好面子是假,骨子里“不吃嗟来之食”的做人硬气才是真。老友酒后说的段子,不论真假,让我好生伤感。不过想起来,它刚好可以与鸡蛋碰糕、羊蹄踢糕、猪尾巴抽糕凑在一起,去印证那个年月中国人过得不易。
说到底,全是那黄糕惹的祸。鸡蛋碰糕,糕是何物?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如在重庆街头到处是麻辣火锅,在西安街头到处都是羊肉泡馍一样,在我家乡那座古老的城市里,街头上到处都有黄糕炖肉,这是家乡的一道风景。我去重庆,那里的朋友请我坐在江边的大排档里吃火锅,虽然不是很清楚这其中之奥妙,却也吃得大汗淋漓;我去西安,西安的朋友请我吃羊肉泡馍,先亲手慢慢地、碎碎地掰馍,再亲口吃,那个香,那个通透劲,也颇有亲身经历一把西北人生活的感觉。晋北一代,黄土高原,几千年之前就盛产黍米。糕,便是黍米面食之精品。这方水土如何滋养这一方人呢?这糕凭着它耐寒、高热的特质,必然是首当其冲、无可替代之物。所谓三十里莜面四十里糕,十里的荞面饿断腰,说的就是糕可以给予人的正能量,远非其它美味佳肴可比。糕是晋北地区特有的,吃过糕的外乡朋友,大都说这黄糕,吃到嘴里没法嚼,越嚼越黏,以致于无法下咽,以致于下次再说吃糕,便婉言谢绝。外乡人不知道,也不轻易相信,享受任何饭菜都讲究细嚼慢咽,可偏偏吃糕不能如此。其实不是我家乡的人生来就有吃糕的咀嚼技巧,而是家乡人吃糕根本就不怎么嚼,只是在嘴巴里随便这么一哗啦就吞下去了。整块整块的糕吞下肚里,再慢慢消化,慢慢地释放它的热量,要不咋就说四十里糕呢。论起吃糕,大同方圆几百里之内都乐此不疲、津津乐道。云州区的父老自然会说,民以食为天,吾以糕为上,糕是我们每天必食之物。我在云州区工作过九个年头,见过吃糕威武者不计其数,有同仁裴氏喜糕兼喜羊肉,他的口头禅是“没羊肉则糕一斤,有羊肉则糕二斤”。裴氏为人耿直热情,身材五大三粗,的确是喝酒和吃糕的高手,他言其父八十高龄,依然可以拿下半斤烧酒一斤糕,令人折服。其他县区的朋友们听后则不以为然,一副按下葫芦浮起瓢,孰高孰低天知道的神态。我一广灵籍学友高氏,长我十岁有余。他多年在外工作,却把广灵的糕面一直带在身边,为的就是这一口。高氏每天下午必有妻子一个电话,问题只有一个,中午吃糕没?那意思就是中午吃了糕,晚上吃不吃糕可以商量,若是中午没吃糕,那晚上必然会蒸好了糕等着他。广灵人吃糕的确厉害,起码我甘拜下风。有一次同事几个出差回来,在路过的一个黄糕馆用餐,做东道主的点过几道菜之后,点了一斤半黄糕。一女士直言道,一斤半糕刚好够我吃,你们要吃就再点吧。常言道人不可貌相,这位美女真就把一斤半糕风卷残云一扫而光。看得我目瞪口呆。我记得这位美女亦是广灵人氏。

巧手蒸花糕
糕分为黄糕、黍子糕。黄糕,黍米去皮磨面蒸糕也;黍子糕,黍米不去皮磨面蒸糕也。困难时期还有黍米不去皮,再加上成倍的糠皮磨面蒸糕的,也能称为黍子糕。不知道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的肠胃,如何能够把这样粗糙的食物吞噬,如今想想都难以下咽。没办法,一个“穷”字可以说明一切。糕,可以把它身为“庶民”,与吃喝拉撒、柴米油盐同在,也可以给它“封官授爵”请上殿堂,与琴棋书画、诗酒花茶一道,成为富贵、高雅的的代表。糕花子便是糕系列食品上得厅堂之“贵妇”。通常讲,食品里带有“花”字的,譬如花卷、麻花等等,不是天生好看,便是制作异常美观,即如花朵绽放一般。糕花子,就是因为其形似菊花或兰花的外表而得此美名。
据说晋北地区在历史上提供给皇家的贡品,有一种小米和几种精致的点心。广灵县有那么一小块土地生产的小米粘香甘甜,成为明清时期为宫廷专供的御米,因此得“东方亮”之称。而那几种点心,至今没人能够找到依据拉出清单。若是让我去选择的话,糕花子和混糖月饼必在其列。一则有特色,纯粹是晋北独一份儿,其它地方不可能见得到;二则好吃,制作考究。混糖月饼是老大同人所爱,好多大同人在外发展或者定居,中秋节里总是惦记着混糖月饼,即如挂念着家乡的父老一样。糕花子,则是那种地道的“出自百姓锅灶,位列朱门餐桌”的甜点上品。我的家乡大同,尤其是老平城的人,很少在家里做蛋糕、桃酥等,个别的时候,比如家里有红白事儿,或者家里来了远亲贵客,才会买几块回来,撑撑门面,表表心意。一般的家里,只会做油面果子和糕花子。油面果子,家乡人干脆就叫果子。就是用烧热了的麻油和糖来和面,做成各种样子,在油锅里缓缓地炸成金黄色,吃起来又甜又酥又脆。油面果子,我想在许多地方都会有,尤其是北方。前些年我在北京和内蒙的老字号糕点行,也可以看得到。而糕花子却只有在我的家乡才能吃得到。油面果子的甜,是因为里面有糖。而糕花子的甜,是黄糕特有的甜,与油面果子的甜完全两回事儿,糕花子的甜是那种很自然、很内涵、似有似无、愈来愈有感觉,心里之甜胜于舌尖之甜的甜。
记得母亲做糕花子,常常是在冬天不太忙的时候。母亲把蒸好的糕,乘着热乎劲加些许白面在案子上揉。加白面是因为糕的黏性太大,不加白面根本没法下手。揉糕是很关键的一环,一直要揉得很筋道。然后在糕团表面抹上麻油,放在那里醒。醒够了,用手一按软软的,才开始用擀面杖去擀。擀糕与擀面不一样,如果糕团醒得不够筋道的话,好不容易擀开了,一不留神就可能又缩回来。

滋滋作响 新鲜现炸的糕

刚出锅的酥脆糕
做糕花子,要把醒好的糕团,擀得越薄越好,最好是比手擀面再薄一倍才好。擀糕是个力气活儿,编糕花子则是个手艺活儿。母亲把擀好的糕,切成宽条,再叠起来切成五条一个五条一个的,然后才去编,编好的糕花子,大致的样子像林黛玉手里的打开了的小折扇,很好看的。母亲一直认为我属于那种手巧的、有些艺术细胞的孩子,所以类似这种活儿,也让我学着做,并且夸我做得挺好。编好的糕花子,不能直接下油锅里炸了就吃,而是要经过一个很长很长时间晾干脱水的过程。晾多长时间呢?我想至少也在十天半个月吧。
晾糕花子,使我联想到装裱字画。过去我上中学时跟一位满口京腔的邢老师学画,记得邢老师画画得好,特别是画那种工笔仕女更是画得很古典很细腻。让我更佩服的是邢老师还会自己装裱字画,怎么上水,怎么上浆糊,怎么绷在一块板上,等等等等,太有讲究了。装裱字画跟做糕花儿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要长时间的晾干,温度低了显然不行,温度高了也不好,最好在适当的恒温之下,效果最佳。记得邢老师裱在板上的字画,怎么也得晾到一周或更长的时间。而母亲晾糕花子的时间则会更长。百姓家里做糕花子,没有专门的地方晾,有些会晾在炕头上,有些会晾在窗台上,下面铺一层干净的报纸,讲究的则在上面铺一层麻纸。晾在炕头上的糕花子,往往要挪来挪去,主要是不能让糕花子下面的热度太高。寒冬腊月难免会把炕烧得很热,热到屁股都无法坐下也是常有的事儿。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就要将花子挪到比较凉快的地方去。母亲说太烫了,糕花子就会表面上干了,而里面的水份就出不来了,那样以后吃起来味道就不纯正了。记得母亲会每天都把这些宝贝翻过来调过去,挪过来移过去,实在没办法,就会用绳儿串起来挂在墙上或柱子上去晾。母亲视这些糕花子如同什么稀罕物件儿,只要有一点点时间,她便会用专门的小扫帚一个一个地去清理,生怕有尘埃落在上面。过了十天半个月,她确认已经干透了,才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一枚一枚地收藏起来。
吃糕花子,一般都是过春节的时候。炸糕花子,一般与炸油面果子一趟车。炸面果子炸的时间会稍长一些,要炸成金黄色,甚至枣红色,才好看,也好吃。而炸糕花子要在炸面果子前,油还没烧太烈时候炸。而且糕花子在油锅里,基本上是打个滚儿,就得往出捞。在油锅里往出捞时,糕花子还是软的,可捞出来过一会儿就又硬又挺了,颜色嫩黄,吃在嘴里既脆又甜。我有一个福建的作家朋友,喜欢收藏紫砂壶,也喜欢烹调。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他家作客,他做了几道菜给我们品尝,同时还开了一瓶从台湾带回来的金门高梁酒。应他的要求,每人都介绍几种家乡的菜或者食品给大家,我当时向大伙说的就是这糕花子。他们说我们以为你一准儿会推荐刀削面给大家,没曾想大同还有糕花子,这样神秘的美食。于是就强烈要求下次来大同,一定要用糕花子待客。出于真诚,我只能报以苦笑。
糕花子虽好,但我确实不知道从哪里可以买得到,可以让我外地的朋友一饱口福。这些年很少能够再吃到糕花子了,老百姓家里很少有人做。年轻人们不要说亲手去做,就是听说过糕花子是怎么回事儿的,也是凤毛麟角。偶然一次,与传达室大爷聊天,竟然看到他的桌子上居然放着一盘异常熟悉而又久违的食物,我不禁说出声来:“糕花子?”
大爷说:“是啊,昨天老伴儿给送过来一些
喜欢吃吗?吃一个!”
“喜欢。吃一个。”
我毫不犹豫地拿起一个,放嘴里轻轻咬下一块,咀嚼,下咽,这是一种很久很久没有过的味道,亲切、甘甜,回味悠长。嘴巴吃着,眼睛和鼻腔里竟然有些发热。
母亲已经离开我们七年了。我有时在梦里看到母亲,她双目失明多年,却可以动作异常熟练地坐在床上捏莜面鱼,一次捏三个,那三个鱼儿从母亲的手心里活蹦乱跳地落在盆里时,我的眼泪唰得流了下来,醒来时浸湿了半边枕头。想起糕花子,不由地想起了我那一辈子辛苦,没过几天好日子的母亲。
母亲,您在哪里,孩儿我想吃糕花子了。

红红火火来做糕
责任编辑:史偌霖
原文地址:http://www.cwzrzz.com/html/2023/1019/27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