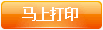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后稷网 > 村委主任网 民俗非遗
老天爷眷顾我们,2022年6月12日这一天并没出现天气预报说的狂风骤雨,反而阳光灿烂,蓝天白云。在阳曲县石庄村的村口,一位放羊倌正赶着他的五百只山羊浩浩荡荡跨过康西公路。
村里的房屋在公路西,羊群过了公路后,便欢快地跃上黄土高坡,羊倌则悠闲地坐在公路边的水泥墩上。他身穿一件蓝色外套,头戴一顶布帽子,胸前抱着一把铁锹,好像抱着护身武器一般。他手上还戴着手套,背上斜挎了一把直柄伞,伞装在布套里。这是夏日标准的放羊装备,简单适用。不管有雨没雨伞要带,不管有风没风外套要穿,也不管有没有活干或有没有危险护身的铁锹要带。
我好奇地抬头看蓝天边上的那些山羊,仿佛落下来的朵朵不安分的白云,有的在低头吃草,有的则跃起来够树叶吃。
康西公路是一条二级公路,南起太原市尖草坪区西村,北至静乐县康家会镇,地跨太原、忻州两市,全长五十二千米。这条公路史称杨广大道,是一条地势险要、商旅愁行的山间古道。如今,天堑变通途,成为连接两地的捷径干道,同时也是一条新的富含人文景观的路。沿线有六郎庙、小天山、杨广栈道、天门关等大小七十二处景,以及历朝历代修建的长城、关隘、垛口等历史遗迹。据史料记载,隋炀帝杨广初为晋王时,开凿了这条经天门关、凌井驿、两岭关、康家会通往静乐、宁武等西北地区的驿道。每年夏天,隋炀帝沿着这条曲折山路,游乐避暑于管涔山上的汾阳宫。该行宫距汾河源头不远,也称汾源宫。但这次我们并没有追溯那段历史,也没有刻意去寻找景观,只是想到公路边的小山村走走。
开车最先到的是阳曲县北小店村,在村委会大院里见到一位正在伺弄菜苗的老农。老农耳背,需要你大声喊叫,才能震醒他。自然从他那里没有获得多少有关村庄的人文信息,还差点被他误导而折返,他说村里没啥可看的,没有我们想看的古建,也没有山溪。网上显示,北小店村有一座清代的小院子,是当年贺龙元帅的路居地。但我们转了一圈,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北小店村的地面比较平整,房屋看起来平淡无奇。于是,我们果断地放弃了它,出村继续沿着康西公路向北开。
路上车辆稀少,有村庄从车窗前掠过,我们没有停,想多往北走走,然后再回返。因为不知道究竟走到哪里算好,便设置了一个折返的时间点。时间点快到时,前方出现修路的工地,我们遇路障被劝返。向修路工打听了一下,前方也确实没啥住人的村庄了。因此,我们连取舍村庄的遗憾都没留下。
欣然调头,路西的第一个村庄就是石庄村。沿着一面沙土坡便下到了村里。如果没有闲情,没有一点乡村情怀,一般人是不会走进这样看起来极其普通的小山村的。
村边有一户盖新房的人家,三个男人正在砌砖墙。路过时,他们向我们看了几眼,都没说话。村子很小,几十米外便是村子的最西头了,有一条浅浅的溪水从北流来。小溪的东岸,一个男人正在洗物品,他问我们来干啥,我们说啥也不干,随便走走。他是唯一一个对我们有兴趣或有警惕心的村人。现在我也没有明白,他只是闲得没人搭讪,还是真的在盘问我们。
跨过溪上的小桥,是一片小小的杨树林,再爬到一侧的土丘上,发现一处被拆除了的院落,面积还不小,留着两眼简陋的小小土窑洞,砖院建筑已全部拆除。地上散落着很少一点旧瓦,还有石井盖,石碾盘,石磙子等。我很喜欢这些农家石制品,在心里将它们直接组装成石茶几。那大小恰好,可以围坐两人、三人、四人。如果我有一处院子,真心想将它们拉走。再说,即便是无人认领,外人要从村里抬大家伙走,总需要一些什么说道吧。
不过,我们还是从废墟上搬走了几块较完整的灰色旧瓦。旧瓦不知有多旧,它们的体型小巧,比平常见的瓦小一号。侯先生可以回家打磨了,在上边刻字玩;我还想到了种多肉的叶插苗。土里还发现一只带猫头的残损筒瓦,猫头完整,图案可爱。将它们统统在小溪流里冲洗干净。又碰到那个爱说话的男人,他问我们拿破瓦干啥,我们说刻字,不知他听懂了没有。
刚走到公路边的车旁边,一回头便看到浩荡的羊群正穿过公路,于是,我们又折回到村口,想拍点羊群照片。但人没有羊跑得快,到村口时,路边只剩下了羊倌,山羊们已经快速跑到高处变成了云朵。与羊倌谈了羊的行情,他自豪地说,五百只山羊都是他的,光剪山羊绒,他一年就能获得纯利润十万元,比在城里做工合算多了。他的神情与言语间透出的幸福和自在深深感染了我们。生活有无数种自洽自得的方式,诗和远方常常显现于风景中。
沿公路向南几百米,路西是将军庄村。没有一个人说得上来村名的含义,村里也不曾出过什么将军。因此我们推断,可能是当年共产党军队的什么将军到过此村,因此叫了将军庄村吧。
将军庄村虽然只有几十口人,但新院落的比例不少,显得很有生机。或许,新院子里住着的多是做项目工程的老板吧。
村北黄土坡上,有一些老旧的窑洞,以为没人住了,爬上去一看,没想到还住着两户人家。一位八十来岁的老头蹲在篱笆墙边的阴影里正在看手机。老人能听明白我们问什么,对话也没什么障碍。村里这个年纪的老人刷智能手机的不多见,过后我们还猜想,他原来或许当过村支书、村长,最少也是一个会计,或是一个老师吧。正值晌午饭时,窑洞里走出一个中年男人,端着碗直接就蹲在旁边吃。我们才意识到,窑洞里早有人在叫老人吃饭,但他一直不好意思离开。他体现的这种古老礼数让我们感动,也深感歉意。他也告诉我们,他没听说过为什么叫将军庄村。村里倒是有一座观音庙,重新修过,原来叫五龙庙。我们顺着他的手指向黄土坡顶瞄了一眼,没上去。
这时,从窑洞里出来一位中年妇女,她来到院子里的水管下洗东西。她说她一般不去庙里烧香,现在去烧香的多是老板们,初一、十五都会开门烧香。问她家养鸡没有,她有些懊丧地说,天热了,鸡都不下蛋了,春天时曾下过一阵。我顿时掐灭了向她买土鸡蛋的念头。
在将军庄村没有发现我们想看的溪水,也没有打听到将军的来由。但因为遇到了老人和中年妇女,我们很是心满意足。老人热情地指出另一条下到村正街的小路,但我们快走到时,发现那条不吭不哈的大黄狗蹲在巷子里,似乎有意识地在等我们。我十分怕狗,为了免遭麻烦,我们又返回到高处,从来时的路回到正街。取车要路过那条有大黄狗的小巷口,胆小的我等在原处,怕惊扰了那条大黄狗。其实都是自心在造作,但我一时克服不了。那条大黄狗自始自终表现得都很温和、安静,是我战胜不了自己的假想敌。
将军庄村的斜对面是海子湾村,位于康西公路的东侧。路边碰到一个叫史平娃的老人,他今年七十七岁。他这样解释村名:村东北有一眼泉,终年不干涸,所以叫海子湾。于是我们按他所指,往村的东北方向走。中途经过两片杨树林,快要延伸到山脚下。但小路上堆满建筑垃圾,立着牌子,是专用的垃圾场。杨树林很大,阳光穿过高处的树梢和树叶,洒在地面形成斑驳阴影,煞有意境。但因为这些垃圾,我们放弃了继续前行的打算。也没有遇到一个人能问,因此神泉最终没找到。回到村里,终于发现一位中年妇女,她一口咬定,神泉早就干了。
回到公路边,史平娃还在。我们将结果告诉他,他信誓旦旦地说神泉还在,就在我们去的那个方向,三面庄稼地围着的一片草地中间,有很小的一个泉眼,他描绘得很有画面感。没找到神泉,老史看起来比我们还遗憾。他十分健谈,主动告诉我们,他有三儿一女,都在城里上班。平时他一个人住在村庄,种糜糜,莜麦,软玉茭,豆角等。有时,孩子们回来,还能带走这些土特产。他家祖籍河南,当年逃荒到了山西静乐县,但那里苦焦,种不了啥好庄稼,所以又南下来到阳曲县,扎下根来。他说在城里住不习惯,孩子们白天上班,他一个人没事干,很无聊,又浪费,所以毅然选择回到村里。除了小麦大米,其他粮食和蔬菜都能种,一个人吃不了,攒下来还能接济城里的孩子们。他觉得很划算。况且村里空气清新,生活轻闲,无压力。何乐而不为呢?老史逻辑清晰地对他的人生做着体悟总结。他也养过羊,一只羊好年成能割二斤羊绒,差时能割七八两羊绒。土塬之上的草质量优于水边的草,羊吃了能长膘。这些知识点都是他主动告知我们的。他滔滔不绝,一只手把住副驾驶座边的窗帮,大有要拽住车以防我们离开的意思。但前边还有村庄要去,我只好打断他的话。他非常识趣,将手一下子就收了回去。车终于启动。老史和我们依依惜别,真诚地说,下次再来时找他,他家就住在土地庙的对面,他用手指了指。原来就在我们车停的边上,有一座大约一平方米的微型建筑物,是村里的土地庙,守着全村人的安康。
这一路上,我们见到的都是老头、老太太和中年妇女。唯记下了老史的名字,他也是唯一一个主动打开话匣子的人。他在城里呆过,又回到村里,与那些一直住在村里的老人似乎不太一样。城市远没有村庄自由自在,但城里的拥挤、繁荣、躁动仿佛也是他生命里的一处亮光。
继续往南走不远,公路西是蔓菁村。村名朴实好玩,或许是村里多种植蔓菁而命名的吧。村口建有高大的拱形牌坊,穿过去,就进入村里。但走不多远,就又到了村外的山脚下。小路边悠闲地坐着几个男人女人,他们身边都放着一捆刚砍下的灌木。田里长的,砍了做柴火,扎篱笆。我们想找小溪,他们说没有。其中的一个男人似乎懂我们心思,他手指了下村北的一块高地,说那里新修了一座三郎庙,原物是清代的。
这些人以为我们是搞摄影的,我们也胡乱答着。如果我们说旅游的,他们打死也不信,因为小山村实在太普通,没有什么景点。偶尔来串串的,也只有那些摄影师了。摄影师更多的是从人文艺术角度,来挖掘呈现这些原生态小山村。我和侯先生完全是率性而来,想在小山小水间解压舒缓疗愈,但骨子里的爱好,让我们更像是一个田野调查者。小山村幸好还在,虽然人气大不如前,但每一位留守的中老年人,他们都懂得本分做人,认真生活,拥有一颗朴素心灵,将山村生活成了部分城里人的诗和远方。
穿过村庄,爬到村北高处,新修的三郎庙门锁着。拐到一边,顺土坡上去,正好踩在了庙院的西厢房顶上。三郎庙是一个小四合院。房檐下立有两块石碑,像是旧物。向东看,绿色远山为辽阔背景,山顶之上是好看的蓝天白云。择另一条土路离开,发现了几丛马兰花,正开着蓝色的花,城里公园的马兰花早在一个月前就已开败了。
有个妇女正从玉米田里往外走,这些玉米半米高,要到秋天才能收获。小时候在农村生活,秋天有金黄色的大个子、粒饱满的传统品种玉米,吃起来香甜又有嚼头,而现在四季都出产的大棚玉米,味道寡淡。妇女说,她种的这些玉米是给羊吃的,她家养了一百多只绵羊,还种了二十多亩地。我们真有些羡慕有地种又有羊养的农户。
绕回到停车的地方,听得背后的妇女大声地跟一位乡人说话,“一看他们就是老板。”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会这样想,我和侯先生从来没有被人认作过老板。妇女可能用一种习惯思维来看我们,因为来村里的外地人多是做产品开发或其他项目的生意人,村庄是他们的办公场所和临时住处。像我和侯先生这样游手好闲之徒,根本无法向村人说明白我们游村目的。
大卜村也在公路西。村名颇有古意,让我们遐想了一番,不知与占卜有无关系。
村里有一处关帝庙,属于当地文保单位。小小的四合院,山门墙壁上残留有字迹,证明原来做过学校。正殿锁着,门缝里可以看到一尊关公塑像。院内有一棵高高的柏树,檐下立着三块老碑,清晰地记载了庙的脉络,此关帝庙于清康熙年间初建,乾隆年间补修,嘉庆年间重修。山门两侧是高高的钟鼓楼,没有钟鼓,山门外对着一座石头基础的老戏台,卷棚顶,戏台上方有木雕的双龙,木色,没有彩绘,古朴典雅。这是今天我们在村庄见到的唯一一座以旧修旧的文物建筑。虽然在山西众多国保、省保面前,它根本排不上名号,但在偏僻的小山村,立着这样一座规整的关帝庙,至少能让人追溯到村庄曾经的信仰。
珍珠卜村则分列于康西公路两侧。村名起得精致,也有一个神秘的卜字。大多房屋在路西,路东的房屋靠着高坡。显然,公路修建后,村庄被一分为二。走到村里,见一大群土鸡正在地上撒欢觅食,其中的一只公鸡见到我们,立马扇着翅膀,咯咯叫着招呼它麾下的母鸡们从一处院门的下方钻了进去。瞬时,地面上只留下另外的五六只母鸡继续淡定地啄食,显然她们不属于那只公鸡家族。那只公鸡不但警惕性高,还是一个责任心强的“丈夫”“大家长”。这是一所石砌窑洞式院落,院门紧锁,主人不在,可以从门缝里看到里边还有其他鸡鸭。我扒着门缝看了一会,一侧头,意外发现门右边是一个窄长的羊圈,四只小羊羔像卧着的四团棉花一样,被我惊扰后,怯怯地站起来,一起惊奇地望向我。
就在我与又白又软萌的小羊羔对视的时候,刚才那只公鸡又带着它的妻妾们从门板下方溜了出来,公鸡万没想到我还在,但它显然已来不及退回到院子里。于是它将计就计,仗着胆子,带着母鸡们迅速跑到远处,边跑边不停地回头看我。它真是一只聪明的公鸡。被这只公鸡带出来的母鸡下的蛋肯定好吃,是真正的土鸡蛋。我在附近想找人打听鸡的主人,但好几家门也都锁着,街上也没碰到一个行人。后来好不容易在地里看到两个妇女,她们告诉我们,养鸡的二子刚刚骑摩托出村了,我们晚了一步。
再往南开,就是西陵井乡政府驻地西陵井村,彻底乡镇化了。越往太原城方向走,村庄的面貌大变,有了排列整齐的、漂亮的别墅式院落,城镇化的农村对我们彻底失去了吸引力。我们向往的农村离城要远一点,它们坐落于山水间,村庄的房屋院落参差不齐,有新有旧,有在房前屋后排排坐的老人,他们尽情地晒太阳,吹山风,透着一份生命的从容、慵懒和自足,劳动过了,勤奋过了,如今成为养老于山水间的留守老人。
也许,他们是传统意义上最后一代扎根农村的中国人,拥有一颗真正的农民心,随顺人生的某种程序,貌似孤独,但内心波澜不惊,仿佛世间的修行者。
而由城里人建设的所谓绿色养老院,虽然也置身于美丽的山水间,置身于村庄和田野中,设施完备,生活方便,但由五湖四海聚集起来的外来城市老人群体,他们怎么可能与土生土长的农村老人比肩生活质量。山风知道,他们永远是这片土地上付着高昂房费的旅客。
与此同时,在城市的角落,拼搏着的一部分年轻人,他们从农村走出去,生活在不属于自己的都市。心有不安,心有不甘。他们早已失去朴实的农民心,但尚没有给自己安置好那颗生命初心。
安土重迁的传统文化早已被时代之风击破,忙忙碌碌的现代人,究竟在何处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归宿呢?
这一天,我们转悠了七八个村庄,一个年轻人也没有看见,更没碰到一个儿童或一个学生模样的少年。村庄彻底成为老年人和中年妇女独享的桃花源。然而,一边是被冷落和遗忘的村落,一边则是令人怦然心动的清风鸣泉、鸟语花香,还有像我和侯先生这样,欣欣然寻找回归之路的旅人。中国农村,经过多次创痛后,结果究竟如何。局部的坚守和临时注射的强心针是否可以打破事物由生到长、由盛而衰的发展规律,是否可以挽留住“50后”“60后”“70后”等人对曾经农村的深情?
人类从乡村开始起步,逐渐发展出城市,乡村和城市曾是人类社会的两只翅膀,代表了退隐和冲锋,柔软和锐利。如今网络化、科技化的凶猛喷发,让人类足不出户遨游虚拟社群,谁还会和谁排排坐在街边的老树下,咀嚼云淡风清的岁月。
责任编辑:史偌霖
原文地址:http://www.cwzrzz.com/html/2023/1019/23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