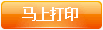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后稷网 > 村委主任网 民俗非遗

长江南岸支流水阳江江畔
水阳江沿着蜿蜒曲折的河道奔流,一艘艘高耸入云的铁驳船矗立在烈阳下,铁驳船在镶嵌着金边的天空下熠熠生辉,偶尔有一簇簇火花飞溅,却被赤红的焊铁面罩阻挡,面罩后是满头大汗的工人们。“刺啦刺啦”是焊接铁船的声音,令人鼓膜震颤,那是刻入我童年的声音。造船工的吵闹声、焊铁声、敲铁声……声声入耳,风从四面八方吹来,把所有的声音吹入蓬草中,忙碌的万物在光芒里微小似剪影。
高亢的蝉鸣声绝对是大多数孩子在暑假里听的最多的声音,但是对于2004年的我而言,嘈杂的焊船声却有着别样的魔力。彼时的我还是个瘦小的男孩,在那个漫长暑假里,焊船声一遍遍回荡在耳膜,回荡在心底,令我忘记了时间。
墙壁上的时针指在了下午两点的位置,我牵动外婆的衣角,像往常一样催促道:“外婆,该去拾铁了。”记忆里的外婆并没有现在的佝偻,鬓发大部分还是乌黑的,她闻言看向屋外,只见那热浪席卷在干裂的土地上,远处的屋舍、树木在热浪中艰难挺立,整个世界都仿佛被罩在熔炉里。

水阳江旁的杂草丛被我和奶奶视作拾铁的“矿藏区”
外婆一边摇头,一边把手覆在我的脑袋上摸了摸说道:“现在日头太毒了,再等等吧。”外婆低缓轻柔的语调像哄稚子入睡的摇篮曲一样。“不要,我现在就要去嘛。”我抓着外婆的手撒娇。她的手掌很粗糙,掌心有裂痕,指腹生着老茧,但我握住那只手时却觉得很踏实、很舒服。
拗不过我,外婆只好回屋去拿帽子,一共两顶,都是农民麦秆草帽,一顶留给自己,另一顶递给我,再拿两条毛巾,浸了凉水又拧干,照例与我平分,随后把湿毛巾搭在头上,再戴上草帽。做好这些准备,她便挎起盖着破布的篮子,领我出门。
外婆家距离造船点并不是很远,都在小镇的边缘地带,以我们这一老一少的脚程,其实只需走上几分钟。但是外婆家在公路的内侧,这边是零星的屋舍与农田,而那些铁驳船全部坐落于公路外侧的江畔上,像是陷入沉睡的巨兽。水阳江虽说是长江的支流,但其实不宽,更像一条大河。
公路上只简单铺了一层石子,这里是偏远的乡镇,不可能像城里一样有斑马线与红绿灯,载客的带棚三轮车与达雅机(一种小型三轮车)常常“嘟嘟嘟”地飞驰而过,扬起漫天尘埃与滚滚黑烟。左右无车,外婆连忙拉着我穿行到公路另一侧,这一侧有很高的圩埂,据说是20世纪十里八乡的农民们用一筐又一筐的土修建起来防止水患的。我们要沿着斜坡土路走下去,才能来到江畔。
外婆驻足的位置其实离铁驳船还有一定的距离,工人们禁止闲杂人员靠近船,一方面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是防止有人偷拿造船的材料。当然,我们本来也不干盗窃那事。这里杂草丛生,大大小小的石块星罗棋布,这里面才是我们要寻找的“矿藏”。来“寻宝”的人大多是一些老人,服饰基本上也是帽子加薄衫。老人们或用手翻动石块,或拨开草叶,或用石片或小铲子挖开泥土,纵使汗流浃背,也在努力寻找。

雪后初霁的湖面晶莹明亮
我看见一位老人从一簇野草里挑拣出一块拇指大小的铁块,明明布满红锈,但在我眼里却闪闪发光,这便是我们要寻找的“宝藏”了——藏在石块、泥土、杂草间的废铁。这些细小锈蚀的废铁,大都不是现在的这几艘铁驳船留下的,而是过去数年里,一代代的造船人遗留的残料,捡拾这些是被造船工允许的。附近的老人没有收入,都过来找废铁卖钱。
外婆遇见了好几个老熟人,连忙笑着打招呼。他们之中有头发斑白的老婆婆,也有身躯佝偻的老翁,别看他们虽然苍老年迈,但是手脚却麻利得很,看到我时不禁感叹:“你这外孙真懂事,放假了还来帮你拾铁。”
也许是心虚,也许是太热了,我用毛巾擦了擦额角,思绪却飘到了老街上的玩具店,我这么卖力地来捡铁,不过是想攒钱买一辆赛车玩具。外婆也没戳穿我,而是和她的老伙计们聊起其他的话题。
孩子有孩子的爱好,老人也有老人们的共同语言,她们从身体哪儿不舒服,聊到谁谁进养老院了,再聊到某个老伙计去世了。从兴致盎然的交谈,到略带忧愁的絮语,最后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老人就像是被岁月一点点侵蚀的铁,对时间与死亡格外敏感。
拾铁,亦非拾铁,对于外婆这辈人来说,这也是一个与同辈人沟通,排遣寂寞的方式。
外婆嘴上说着话,手上的功夫却未曾停歇,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外婆的篮子,那里已经放了好几块废铁,都是她从石块里翻找到的,可我却听她们聊天听得太入神,一块铁都还没捡到呢。
这里没几棵树,自然也没有蝉鸣,只有附近造船工用电焊机焊接钢铁的声音和用铁锤敲击铁板的声音。我习惯了这样嘈杂而响亮的声音,就像城里的孩子习惯了清脆空灵的钢琴声与悠扬婉转的小提琴声。
我集中精神,一块块搬开石头,开始认真搜寻废铁。这里的铁块经过老人们好几轮“扫荡”,大部分都被人捡走了,余下的并没有那么多,有时候要挖很深才能找到一块,但更多时候是翻找很久也无收获,我固执地在一个地点翻找许久,终于在层层叠叠的石块下发现一块巴掌大小的铁,这已经算是很大块的了。
它埋得那么深,不知道是哪一年从铁驳船上滚落,也不知道被遗忘了多久,岁岁年年,它的兄弟姐妹们也许已经随大船一起驶入江海,看过无数绮丽的风景,而它却被困在阴暗狭窄的礁石里不见天日,这是何等遗憾。
好在我把它挖出来了,小小的铁块将会跟着废品站的运输车前往五湖四海。它也许会成为钢筋,支撑起钢铁城市,也许会变成螺丝钉,帮助机器运转,那是更加广阔与精彩的世界。
外婆还在和老人们说着话,隐约能听见什么小孩子要好好学习,以后争取考个北京、上海的好大学之类的话,我并没有在意她们的谈话内容,考大学什么的太过遥远,至于北京、上海之类的大都市就更加遥远了。现在的我,不过是这偏远小镇里一个最普通的小学生,谁会在意那么遥远、那么虚无缥缈的未来呢?
嘈杂的焊船声里,我心无旁骛地拾铁,心里充斥着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安宁。
时间仿佛是凝固的琥珀,明明无比漫长,却转瞬即逝。很快金乌西坠,耀眼的太阳一点点变得柔和、暗淡,化作金红色的霞光,散落在云团里。焊船声也渐渐平息下去,工人们都下工去吃晚饭了,外婆也挎起篮子说:“走吧,该回家了。”
夕阳下,一只粗糙的大手牵起稚嫩的小手,一高一矮祖孙俩的身影被霞光拉长,延伸至身后摇曳的蓬草中。矗立在水阳江畔的铁驳船如同无声的雕塑,一直目送着我们离去。
之后的暑假里,我隔三岔五地就跟着外婆到江滩上去拾铁,一天一天机械地重复着。外婆会按照收废品的标准价格“收购”我捡到的铁块,一毛、两毛、一块、两块……我床头的存钱罐也越来越满。当然,作为代价,我也被毒辣的太阳烤成了“小包拯”。
开学前夕,我终于攒够了买赛车玩具的钱,正当我思索着应该买个什么款式的赛车时,外婆突然笑眯眯地出现在我眼前,手中捧着一辆崭新的“冲锋战神”赛车。那一刻,我觉得她就像《大话西游》里的至尊宝一样,踩着七彩祥云从天而降。外婆总是默默关注着我,尽其所能满足我的所有心愿。
很多年后,我已经长成了肩负责任的大人,就如同曾经外婆期待的那样,去了大都市工作,只有放假才能回家看望她。外婆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门前,见到我会情不自禁地露出笑容,她脸上的沟壑愈发深邃,身形也愈发佝偻了。金色的阳光下,我仿佛又回到了2004年的那个暑假,回到了与外婆一起拾铁的旧时光。
责任编辑:史偌霖
原文地址:http://www.cwzrzz.com/html/2023/1019/22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