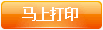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后稷网 > 村委主任网 民俗非遗

平座远景
平座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是一个隐藏在大山里的自然村落。故乡的影子,在一个个山头上,在一列列梯田里,在久远的记忆深处。
一
我的故乡,是十二世祖文官公从繁峙城小关庙街迁来,开荒、盖房、建设家园,起名平座,距今已二百八十多年。故乡位于恒山西余脉北麓,坐落在一个山坳间。坐北朝南三面环山,背靠山丘(俗称房圪脑),而且特别向阳的世外之地,东西两侧泉水烘托。东侧大泉沟和西侧品泉沟流淌着清澈爽凉的泉水,痴痴缠缠的守护在村的两边,最后汇聚在中锥流向叫西贾庄那个遥远的地方。
平座,顾名思义,应该是特别平坦的意思。然而来过我家乡的亲戚朋友都会感叹:平座不平啊!从西贾庄峪口顺着清凌凌的泉水碰撞石头的声音,走大约八里的路程。还不时地有山圪叠,爬上石阶,继续向前走,从泉水的这边跳到那边,回旋过来再从那边跳到这边儿来,泉水蜿蜒清冽,山花倒影,走着走着, 会让你觉得走进鸟语花香,置身于仙境的山涧幽径。泉水里有小蝌蚪,有青蛙,有飞舞的花蝴蝶从眼前掠过。有时走着走着冷不防,会有一条青蛇或者是黑蛇赤裸裸的拦截在你的脚下,这时别惊呼也别乱动,屏住呼吸安静的走开,即相安无事。要是被吓昏了头脑,蛇也会活蹦乱跳起来,让你的心提到嗓子眼上,头发一炸一炸的站立起来,吓破胆。再向前是最高的一个山叠, 有瀑布溅落下来,那泉水叮咚锵锵跌滑在发白的大石头上,瀑布的一侧有自然形成的台阶,沿着阶石使劲的迈上去,这一刻最清爽,不时地有水花溅在头发上衣服上甚至鼻尖儿上,顺着嘴角进到嘴里,那甜丝丝的滋味流入心里。这时干脆蹲下来双手捧泉水喝上几口,更加的凉快。那山沟海拔随着每个圪叠高度而增高, 越往前走泉水越阔,也更加清澈,泉水声愈加的洪亮, 这是夏天。要是冬天,那泉水都结成冰,白茫茫的冰把整个山沟覆盖的严严实实,光滑的如镜面,如若有飞机从西贾庄峪口到中椎梁航拍,那宛如一条洁白如玉的飘带曲曲折折呈现出来,美到极致。想要走到中椎坡脚下,还需要有经验的长者走在前面用土洒路, 方能行走。不然冰滑的走一步会跌一个爬都爬不起来的骨碌。大约再走二十分钟,就到了中椎梁下。有一块四方大青石,也不知躺在这里多少年代了,过往的人都要在上面歇歇脚。
这段形如登天的路,应该叫羊肠小道最恰当不过。那坡陡峭程度没有 90 度也接近 70 度吧!直立立的中椎梁挡在眼前,抬眼望去,梁顶与蓝天白云相接。要想回家必须爬上这梁,深呼吸一下,鼓足了勇气向上攀爬。气喘呼呼的爬上半坡歇息,远远望去山沟的清泉流淌,真后悔刚才没把泉水喝个够。我们走熟惯了, 也得拽着沙棘树或者是荆棘草,随着 Z 字路爬上去, 足足得用三十分钟。要是第一次来我们村,那可苦了, 走一会缓一缓,一个小时爬到中椎梁上时,已经累的不成样了。抹着汗会很懊悔的说一句:下次再也不来了!可奇怪的是,从我妈到婶子大娘们大部分是从西贾庄以外叫川的地方嫁来的。
爬上中椎梁都会歇会,夹背的汗被山风吹的凉飕飕的打个寒颤。继续向前是二圪梁三圪梁,过一个圪梁梁一个湾又一个圪梁梁。那圪梁梁一个比一个高, 一会从梁的左边走过去,又穿到下一个圪梁梁的右边。真是几座山圪梁梁几道道弯。山梁的两边是梯田,有随风翻卷的莜麦浪,金黄色的油菜花开了满地,各种颜色的山蛋花嫩油油的随山风摇晃着。山坡上到处是药材黄芪,遍地的野花,背阴处长满沙棘树。总会扎一个五颜六色的大花环戴在头上或者是脖子上,手里拿一束红色的山丹丹花。要是冬天沙棘树上挂满了酸甜酸甜的沙棘果,坐在沙棘树下,咬一嘴沙棘粒,有时会酸溜溜的打个激灵。不禁感叹“曲径通幽处,家山花木深”啊!
二
几经辗转,汗流浃背的总算走到了房圪脑。全村共十二个院落,包括我们的学校,住着十四户人家。
村前有羊圈梁作屏风,后有房圪脑当靠山。房圪脑东西都有进村的路,左边东藏头走进村到了五奶奶的石头墙根脚下,右边西藏头进村到达三大娘房顶后。这时会听到鸟鸣鸡叫,三婶婶家的大黄狗也会汪汪地叫上几声。映入眼帘的是绿树成荫的羊圈梁,当暖地一层层的梯田,还有一片片的银杏树,镶嵌在羊圈梁的阴面。
沐浴在山风中,暖阳下的四排房,靠着房圪脑顺次排列下去。后两排属于老房子,后墙直接靠着山,用石头一块一块垒砌而成。我的家独自在第三排,用精泥打成土坯,修砌成一出水四间平房。我家房西有条直通学校(第四排房)的路,路边用石头垒起的花栏墙,既美观,娃娃们上学又安全,其实我家和学校是房前院后的距离。路西那块地叫西三亩地,种植山蛋,在西三亩地靠路边银锁哥房前(第二排),有一碾磨细粮的磨盘, 没顶,四周土抷起来的墙,全村老小都叫磨坊。哥在山外很远的地方上学,被饿的面黄肌瘦。母亲心疼着,着急着。就把各种豆子炒熟,比如豌豆、黑豆,混合起来背到磨坊碾磨成面。从石磨漏眼灌进去,先压成四六瓣, 反复好几次碾压,才成了面。就这样,母亲还得用细纱箩再筛一遍才行。母亲说这混合起来的面叫“炒面”。帮母亲推磨一会一口豆子,一会一嘴炒面。炒面香喷喷, 豆子咬起来嘎嘣响。回头看看母亲,额头渗出的汗水已经浸湿了头发,一缕缕粘贴在她的鬓角。母亲还说:“哥不饿了,学习就有劲。”娘俩推磨时的速度不由得加快。当哥喝一碗热乎乎的炒面时,端起的何尝不是沉甸甸的母爱呢?

村落一角

贫瘠的土地
我家左边藏圪洞,这块土地肥沃,泥土总是湿润润的,家家户户栽葱或者泥炕用土时,就在这里挖, 慢慢的成了深凹。后来爸在藏圪洞靠右盖起新房,藏圪洞自然也成了我家的自留地。年年种山蛋,年年长势惊人,那山蛋又沙又甜。
藏圪洞前是三奶奶、四婶婶、还有唯一一家外姓马德周表大爷的家。学校紧挨表大爷,有一堵高高的土墙间隔。三奶奶单独院落,四婶婶和表大爷火院,可红火了,他们饭熟后,就端着碗,圪蹴在院子的石头上, 边吃饭边说家长里短,笑声总是从这个院子里飘荡在全村。四婶婶养着一条黑毛毛白眼圈的狗,让我不敢进院, 就爬在学校那堵墙上,看他们吃饭听他们讲故事。
在三奶奶家和藏圪洞东有条通往黑土湾和大泉沟的路。路那边是四亩地,四亩地顶端有全村集体养殖园, 大概是我祖文官公早就规划好的吧。让人和牲畜分离。每家轮流着打扫养殖园的卫生,这是老辈们留下来的规矩。养殖园共两排房,土墙间隔,各家的牛羊骡子, 晚上地里归来,回到属于自己的圈里,从不乱串。村里的长辈们把门关上,回家歇息,以备第二天上山劳作的精力。
紧挨着养殖园,在当暖地最宽的那块地,呈半椭圆形,像是羊圈梁的底座,挖着一排排每家每户储蓄山蛋的窖。窖的周围有很多银杏树,这些杏树各家也分的很清楚。我们这些娃娃们各守规矩,只摘自家树的杏。最惹人的是大爷家的那颗大瘪瓜杏树,那大瘪瓜杏吃起来既甜又是水灵灵的干壳,有小拳头那么大, 而且杏核子都是甜的。我们这些娃娃们也只是抬起头用馋人的眼神眊一眊,馋的严重时巴扎巴扎几下嘴唇。有时遇到大爷,会微笑着给我们摘上几个,娃娃们不舍得吃,把大瘪瓜杏装在裤兜兜里,就是吃了也把杏核子拿回家,再悄悄的种在自家地里,盼望着也能快速地给长出一棵大瘪瓜杏树来。

磨盘
平座村全部是干旱的山坡地,以种植山蛋、莜麦、豌豆为主。所以储蓄山蛋已成规模,秋收时有很多山外面来的人买我们的大面山蛋。在当暖地那场面又是一番喜人的景象。银锁哥捉称,福锁大哥记账,一家山蛋称完,再称下一家,其乐融融,互帮互助。我们这些娃娃们也忙着穿来串去,张袋子口,挽麻袋绳。我祖文官公看到这场景,一定会欣慰的点点头,微笑着更加福佑他的子孙后代。
三
故乡的水清、山好、人更暖。平座经历二百八十多年的成长与沉淀,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有多少张氏子孙在极其偏僻艰苦的环境中,用勤劳的骨骼战胜大山,过着安稳自给自足的生活。
晨雾渺渺,在鸡叫五更时,轻绵绵的炊烟就会准时漂浮在村子上空,形成一幅淡墨轻描的画卷。由于山高路远,“电”对于平座村是陌生的概念,晚上照亮全靠煤油灯。当时煤油是昂贵的,所以各家各户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
那个时候,爸在山外面打拼自己的事业,家的里里外外全部由母亲担起。母亲总是起的最早,睡的最晚。白天下地干活劳累一整天,晚上还得在煤油灯前缝缝补补。秋收后,更需要熬夜磨山蛋澄粉面,有时会把手擦破,山蛋冰凉手也冰凉,用更冰凉的山泉水打澄粉面, 当把多余的山蛋磨完时,母亲的手指暴着裂,皮肤发黑, 双手早已伤痕累累。那时的母亲总会有一缕头发随着劳作的每个动作摇摆,母亲搂起那一缕发的时间都好像是特别宝贵。
母亲还带动村里的婶婶大娘们搞副业,养猪养兔。这收入是家里最大的一笔财富。母亲把澄粉面留下的残渣,煮熟喂猪,上山干活时捎带着给兔子,拔些绿茵茵的草。母亲忙时,这些拔草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姐妹仨。那兔子白色的、灰色的、黑色的,可爱极了。猪和兔养大时,妯娌好几个相跟上,赶着猪,用笼子背着兔, 到西贾庄去卖。那个时候,母亲会给我们姐妹仨买回几尺红头绳、粉头绳,姐妹仨挣着抢着挽在辫子上, 娘几个开心地笑声不停。
担水是平座村男人们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情。天刚蒙蒙亮时,爷爷就去一里外的泉子沟的泉眼担水。爷爷是我的亲爷爷但不是爸的亲爹。爷爷不爱说话,眯缝着眼睛,爷爷是个实打实的硬汉子。他回来会在我家门外咳嗽两声,母亲忙着去开门,爷爷把第一担水倒进水瓮里,也不说话立马返回给婶婶家挑第二担水。
当母亲做变样饭时,就会让我们喊爷爷来吃饭。我们兄妹四个争着去,坐上靠在房西墙的梯子档中间喊: 爷爷、爷爷。爷爷住在婶婶家的东屋,婶婶家在靠山第一排右边,一堂两屋,看到爷爷走出门来,我们才停止吆喝。母亲会把第一碗菜端给爷爷,要是有肉,爷爷碗里那层肉一定是最厚的。爷爷哪里吃得下,会挨个的把肉夹在我们兄妹的碗中,吃完饭抚摸下我们的头,着急的下地干活去了。有时看见我家的生火柴不多时,干完活会背一背的圪针柴,悄无声息地放在我家柴堆旁。
大山是温暖的,却也有苦涩不堪的味道。住在大山里,全靠“背山”才有饭吃。粮食和生活用品都是从地里或者是山外面背回来的,所以村里的男人们大部分时间停留在自家地里忙碌着,除了全村开会,商议大事,平时是很难见到人影儿的。爷爷总是说:咱村的男人们苦太重寿命短。大泉沟和品泉沟对面那山上一条一条的莜麦地,都是父辈们用镢头,一镢一镢种下去,用脊梁,一脊梁一脊梁背回来。莜麦捆起来,男人背三捆,女人背两捆,孩子们背一捆。从那边的地背下山,走到沟里, 再从沟背着上山,背回山上村里的场面。他们的汗水从发根顺着脖子流在前心和后背,体内的血液翻滚着像烧开的水,在沸腾、在回旋、在喘息。
五爷爷五十多,紫糖色的四方脸,精细勤劳性格憨厚话语少。住在我家后面,四个男孩两个女孩。五爷爷家的孩子最多,院子在村里也最大,用土抷起来的墙整整齐齐,院内种的杏树梨树苹果树,还有桃树上的大仙桃,让人看见就眼馋。然而五爷爷却不堪重负劳累过度,得了急病,由于交通阻碍无法找医生及时救治,一米八高的汉子被大山压弯倒了下去,一口气过去再也没有醒来。那一刻五奶奶的天塌了,嚎啕大哭,全村大小处于沉痛当中,大山也为之动摇悲叹。全村人帮衬着让五爷爷得以安息,就此羸弱的五奶奶独自扛起扶养六个孩子的责任。五奶奶渐渐的也变得强大起来,成为全村最强的女汉子。
睿智的祖文官公留给子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就是: 勤劳朴实纯善。大山虽很沉重,但战胜困难,吃苦耐劳是张氏子孙从骨子里迸发出来的力量。在粮食最缺乏的那些年,平座村没有饥饿。用一把镢头开垦出更多的土地,虽然减产,仍然能够自给自足。山里男娃娶媳妇难,而平座村没有一个光棍汉。自古说得好“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我母亲我婶婶三婶婶和四婶婶都是从山外面平川嫁来的。她们慢慢的不怕行路难, 很快成了山里人,过上了有吃有喝的日子,还不时的接济娘家来的人。一位远方亲戚马表大爷佝偻着带了三个儿子和表大娘爬上山来,恳切的要来安家落户, 说在山外无法生活,饿的慌。长辈们集体商议决定让表大爷留下来,多少年来张氏家族是从不留外姓人啊! 慈善的平座村人,每家都让出自己的地分给表大爷, 还给选好宅基地,帮助盖起了新房。表大爷腰直了起来, 表大娘每天乐呵呵的给我们讲故事,梳头发编辫子。世外的平座村其乐融融,草更绿山更清。而我们这些山里娃每天放牛放羊,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爸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爸在外面闯世界,眼界比较宽广, 平座村最缺失的是教育!打听到全公社最出名的李存贵老师,特意邀请来,办起了学校。这些山娃娃有了归属。李老师来了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起了温文尔雅的新名字,后来还盖起新学校,山娃们的读书声在山风中那是越来越响亮。为了让李老师安心教娃娃们, 村里长辈们决定把黑土湾那块最肥沃的土地让李老师种山蛋,来贴补家用。李老师在平座村一呆就是十八年。李老师整整十八年的功夫,让山里娃走出山门,考上了大学,有了工作,改变了全村的原始状态。
四
由于人和牲畜分离,平座村干净整洁,空气清新。我从姥姥家拿回格桑花种子,种在学校墙背后一溜空地上,担水浇花。那时才明白,村里的旱地不能种菜, 离泉子沟太远,绿色蔬菜需要浇充足的水才能长好,长辈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挑那么多的水。而我精心浇灌的格桑花很快长高,各种颜色的花一天一个样儿的在山风中开放,鲜艳夺目,惹来蜜蜂,惹来花蝴蝶,也惹来村里的娃娃们围着花转。第二年也不用种格桑花了, 格桑花自己在村子里的角角落落生长开花。由此对格桑花有了一份特别的情感,而我收获最大的还是学会了担水。爷爷忙不过来,母亲上山干活,我家水瓮经常出现底朝天,母亲干活回来做饭时看看没水,才挑起扁担去担水,我小小的心像被山里的大石头撞击似的深痛深痛。放学后,借助要浇格桑花,先给水瓮倒两半桶水,再返去一里外的泉子沟担水浇格桑花。有时天太黑,周围没有一个人影子,山风呼呼怪响,吓的我放下扁担撒腿往回家跑。第二天爷爷背抄着手走到泉子沟,拾起扁担挑回满满的两桶水,倒在我家的水瓮里。去泉子沟是一条比较平坦的小路,泉子沟在黄剑草暖和二中涧的一个深沟里,泉眼在半山腰,用石头垒起来的小水窝窝,泉水嘟嘟的冒出来,也不外溢,刚刚够全村人的吃水。从泉眼渗下去的水形成小溪,长辈们在小溪边开挖出一块块小菜畦,种各种绿色蔬菜,有黄花、韭菜、萝卜、菠菜、芹菜、茄子应有尽有,在担水时摘上一天足够吃的菜。大泉沟和品泉沟种着大白菜和卷心白,那是为过冬储蓄的菜。泉眼里的水特别神奇,再干旱的天也是满满的,菜席里的菜也是绿油油嫩盛盛,这样平座村的人们喝着山泉水,吃着天然的绿色蔬菜,安居乐业代代延绵,咋感觉都是文官公在护佑他的子孙血脉。一切都是刚刚好。
五
然而随着时间的前行,平座山坡陡峭,交通极度贫瘠的土地闭塞,落后的面貌无法改变。山娃娃们需要更高的教育,深山里先辈们开垦的那些贫瘠的土地,再也无法承载后辈的更多希望,山外飞速发展的世界,动摇着平座村快三百年的自给自足的原始生活状态,震撼着张氏子孙寻求发展的那颗不安的心。痛定思变,整体搬迁,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接纳。只好逐渐各自寻找门路,搬到或远或近山外的乡村,散落在各地。张家人被扯的四分五裂,那种分离的痛,深深的印烙在羊圈梁与房圪脑山坳间。渐渐的,平座村听不到鸡鸣狗吠的声音,也看不到夕阳西落,袅袅炊烟唤儿回的景象。村子悄无声息,田地荒芜,房屋开始哭啼,慢慢的直立不起来,东倒西塌。只剩下当暖地那些银杏树,没有炊烟的熏染,甜蜜的大瘪瓜杏也失去了原有的味道,那些苍老的银杏树在狂风中发着哀叹的怒嚎,碾磨在寂寥中被山风侵蚀着身首分离,只有羊圈梁房圪脑仍然守护着故乡仅留存下来的残垣断壁,守望着远去的人偶然归来。
故乡渐渐的低垂沉默下去,被时代抛却,被时光遗弃,失落在山风中再也无法拾起,从此血脉靠一本家谱相连。那一抹乡愁在落日中升温,那厚重的记忆萦绕在思乡的魂梦里。
责任编辑:史偌霖
原文地址:http://www.cwzrzz.com/html/2023/1019/2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