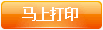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后稷网 > 文化产业网 民俗非遗
金代儒学源流众多,其中,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经学方法总结的唐代经学对金代儒学有丰富而深刻的影 响。唐代经学首先辅助推动金代儒学早期普及化和中期制度化,并为金代儒学的勃兴提供了基础的思想材料和成 熟的体系模范。在进入晚期学术化阶段后,早期对唐代经学的学习吸收仍然在规范金代儒学的学术内容,如尚中 意识和三教融合等。此外,唐代经学也影响着金代儒学经世致用与批判疑古的精神风气,进而在金政权消亡后为 后学所消化继承。通过梳理唐代经学对金代儒学的影响,可以看出金代儒学本身发展的独特状貌是有迹可循、有 所继承的,从而消除其理论形态发展的孤立性。
金代女真政权非常注重学习吸收先进的中原文化。 在思想方面,接纳学习儒学是汉化的基本,成熟 的唐代经学由于承继政治正统,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金代 早期确立了对唐统的继承,因此在文化政策上大力推行对唐 代经学的借鉴吸收。金代在封建化改革过程中,虽然在诸多 政策上唐、宋、辽兼采,但其承辽绍唐的执政方针贯穿始 终,其教育、制度和学术研究的基本内容带有鲜明的唐代经 学色彩。
儒学制度的完善
据以往学者分析,金代儒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金初太祖太宗时期“借才异代”的普及化阶段、金中 期熙宗至章宗统治前期的制度化阶段和章宗统治后期开始 的学术化阶段。金代太宗朝始有科举。天会元年(1123) 举行了金代初次科举考试,此后,天会二年(1124)二 月、八月及天会三年(1125)再举,但此时的科考制度尚 未成熟,时间地点人选皆无定规。天眷元年(1138)开经义、词赋二科取士;天眷三年(1140)于上京建孔庙,同 时诏令宗室子弟阅读儒家典籍。在中央官学之外,民间私 学也从未消匿,民间经学、洛学、蜀学甚至王氏新学都有 流传。但从宏观角度来看,金初规定的官方教育思想还是 较为成熟的唐代经学,尽管这一时期的科举制度并不完善 且多有弊病,但是它仍作为最重要的载体延续了唐代经学 在北方的微薄血脉。 进入“大定、明昌之治”时期,金世宗、章宗在前期 统治者初建教育的基础上,继续仿照唐制完善教育与科举制 度。唐代在中央设“六学二馆”,在地方设州、县、乡、里 四级并立的学校制度,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央与地方紧密衔接 的官学教育体系。与此相比,金世宗于大定六年(1166) 扩充太学达四百人,形成了金代中央官学的大体规模;在地 方官学层面,于大定十六年(1176)设立17处府学,又于 大定二十九年(1189)增设7处。据薛瑞兆估算,金代地方 官学培养人才大凡有千八百人。这表明金代官学基本建成了中央—地方全面完整的体系。 金代官学的教学内容仍以传统唐代经学为主。唐代经 学课程以《孝经》《论语》为必修教材,另以《左传》《礼 记》《毛诗》《周礼》《仪礼》《周易》《公羊》《穀梁》 《尚书》为专修教材。金代官学仿之教授词赋、经义。针对 儒家经典,金代官学教材选用唐代经学规范注本,授学对象 包括女真族、汉族、契丹族等。与辽代限制契丹族进行儒学 学习不同,金代统治者十分重视本族儒学教育,于中央设置 女真国子学,地方上则设女真府、州学。至此,金代官方主 导的儒学教育实现了在东北地区的基本覆盖。由此,唐代经 学借助金代官方教育体系这一可靠载体实现了向东北地区的 传播,初步影响了这一地区后来的儒学发展形态。 与教育制度建设同步进行的是科举制度的完善。金代 科举的绝大多数科目都关涉儒学,其中明经、经义二科皆以 唐规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经义考试重点考查正确注解后的 发明义理,明经考试则重点考查注疏的正确性。唐有童子 科,或称神童科,北宋时不甚重之,金代经童科则对其有所 发展。女真进士科的主要考查内容是由汉文转译为女真文的 五经。而词赋科是金代科举最重要的科目,人数最多,待遇 最优,考试范围包括《孝经》《论语》《孟子》及《荀子》 等儒家经典。金代科举的成果十分可观,薛瑞兆在《金代科 举》一书中整理得出,金代科举考试大概有四十七次,其 中,词赋进士四十五次,经义进士二十六次,策论十六次, 取士约六千余人。 金代中期统治者借鉴唐制,完善官学教育和科举制 度,一方面是因为唐代经学教育成熟适用,另一方面也是 “承辽绍唐”执政方针影响下必然的政治举措。这样一 来,以唐代经学为主的儒学作为一种成熟的知识体系充实 了金代科举考试内容,并加强了其在北方地区的传播普及 与延续。
学术内容的继承
在完成了吸收利用唐代经学以推动女真汉化和充实完 善教育和科举制度之后,金代儒学内部的发展重新开始运 作。随着政治统治体制化的逐步稳定,金代儒士得以摆脱 政治任务的桎梏,着手建构独特的儒学形态,其在建构过 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唐代经学的启发与影响。 首先被继承的是唐代经学的尚中意识,《礼记·中 庸》一章没有受到汉儒的足够关注,直到唐代《五经正 义》撰成方有改观。《礼记正义》以君臣关系为新的理论 突破点,首开“沿忠恕的路径将外在的纲纪内化为个体之 心”的方法路径。而对于作为基本概念的“中庸”的理 解,《礼记正义》秉持“疏不破注”的原则,继承了郑玄 注“庸,常也;用中以为常道也”和何晏注“庸,常也;中 和可行之常德”的解释,以“常”训“庸”,以“用中为常”解释“中庸”。金代大儒赵秉文、李纯甫等都对“中 庸”“中”等思想十分重视,皆有独特阐发。 “中”在金代大儒赵秉文的思想中无处不在,他曾 作《中说》《庸说》《和说》等篇详细阐述。与《五经正 义》孔疏的思路相同,他从维护统治的目的出发,格外强 调中庸。在赵秉文看来,“常”代表着“百世常之道”的 “亲亲、长长、贵贵、尊贤”的伦理道德标准,而能稳固 这一套标准长久不变的是“时中”,“时中”因时而变最 终达到“和”。赵秉文对“中”的理解建立在对韩愈人性 论的反思之上,他认为韩愈所言性上、中、下三品,指的 是性之才而非性之本,提出“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认 为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才是性之本体。 李纯甫对《中庸》文本和“中庸”思想的理解主要 受到李翱《复性书》的影响。李翱对《中庸》的阐发很是 系统完备,《复性书》主要源于儒家《中庸》和佛教心性 论的融合,他批判继承韩愈的“性三品”说,试图以《中 庸》为理论基础发展孟子的“性善论”。李翱认为“性” 与“情”的关系是“性善情恶”“情由性生”,要想实现 “复性”,即由恶向善,关键在于“尽性”“至诚”。李 纯甫也遵循这一思路,将中庸思想用于三教合流的思想建 设上。李纯甫认为性与情二分。他认为圣人之性与常人之 性相同,但圣人之情与常人之情不同,所以“圣人能致中 和”。他赞同李翱“圣人有性未尝有情”的说法,并认为 这一观点出自庄子,所以庄子的道家思想与儒、佛相通。 李纯甫的这一论点引出了三教合流的大趋势,唐代教育 制度和内容表现出明显的三教融合态度。首先是《道德经》 被列为科举科目;玄宗开元年间曾设玄学博士,令其习《老 子》《庄子》《文子》《列子》等,在教育制度层面确立了 道教思想的地位。另外,无论是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还 是孔颖达等编撰的《五经正义》这样的官方经学通典,无一 例外都包含了《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前文提到,陆 德明的《经典释文》儒道兼通,孔颖达等编撰的《五经正 义》兼有儒、释、道等秦汉魏晋南北朝各种主流思想。这便 在教育内容层面决定了三教融合的方针。从唐代学术思想中 也能明显看出三教融合的踪迹。韩愈借佛教法统说创儒家道 统论,对佛道“治心”产生共鸣而创新儒学心性论;其弟子 李翱充分发挥孟子心性论内容,援佛入儒而作《复性书》; 同时期的柳宗元也以主张“综合儒释”闻名。总而言之,唐 代经学的学术内涵中本就兼有儒、释、道的无限可能性,这 种可能性是这一时期三教融合大趋势的具体反映。这使得学 习吸收唐代经学思想养分的金代儒学在自觉或不自觉中继承 了三教融合的传统。
精神风气的熏陶
《中庸》记载:“力行近乎仁。”经世致用是儒家的一项基本精神。作为学习模板,唐代经学的经世致用特 性也在金代儒学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唐代中期的《春 秋》新学派面对王朝将颓的局面,号召“以宜救乱”;韩 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也积极呼吁救世,并将学术思想 转化为政治实践“永贞革新”。金儒赵秉文也是一位经学 大家,只可惜其诸多解经著作没有留传下来,我们只能从 其关于“道”的思想论述中窥见其倡实用之精神。赵秉 文将“致知”与“力行”喻为“车之两轮,鸟之二翼, 缺一不可”。他认为真正的“道”必须贴近人伦日用; “道”并不过高难行,“清虚寂灭之道,绝世离伦,非切 于日用”,人们对这种不切实际的“道”可以自行取舍, 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样的伦理道德法是“大 经”,人生不能脱离其而存在,即所谓“可离非道也”。 赵秉文的时事策论表现出了强烈的变通意识。金代“贞祐 南渡”之后,面对大厦将倾的危局,赵秉文力主救世,并 提出了类似宜从权变的主张,“大抵有天下者,安必虑 危,治必防乱,所以长安且治”。
王若虚毫无疑问也是金儒中贯彻“通经致用”精神的 代表。他的学术根基是唐代经学,他自幼接受唐代经学教 育,所吸收的儒学材料源于金代被奉为主流的唐代经学。 在对前代思想的认识上,他既不满早期唐代经学的僵化死 板,也不满北宋理学的过分抽象;他赞同唐代中期《春 秋》新学提出的主张“通经致用”以追求“外王”的观 点。王若虚解经力主“通经致用”,反对北宋理学重“内 圣”、“经以载道”的解经理路。他认为宋儒解经“消息 过深,揄扬过侈,以为句句必涵养气象,事事皆关造化, 将以尊圣人不免反累”。他认为圣人设教使人“识天理” 的手段是外王之路,“圣人虽无名利之心,然常就名利以 诱人,使之由人欲而识天理,故虽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 兹其所以为教之周也”,主张圣人以利诱义。更能体现王 若虚求实精神的是他的“人情”说。“人情”即人之常 情。王若虚认为圣人与常人无异,其日用常行一定合乎常 理,“盖君子之道,人情而已……不近人情,便非君子之 道”。由此,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以“人情”解经的思 路,即理解经文中记载的圣人言行,只能也必须从人之常 情出发。王若虚“人情”说的真实内涵在于,宁可拘执于 语词本身的含义,也不能脱离实际妄加推测,这深刻反映 了王若虚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 金代晚期儒学进入全面学术化阶段,这一时期,伴随 政治上的危局和南宋儒学的渗透,金儒开始转入对唐代经 学,尤其是对唐代早期传统经学的批判。除了唐代早期经 学为金儒提供了批判材料之外,唐代中期经学中出现的疑 古批判思潮也受到了金儒的高度评价与肯定。金末的儒学 家们在上述思想基础上做出了难能可贵的学术创造。
经世致用风气的另一面便是适时的批判疑古,以实现 合乎当下的改革,而对传统经学模式的批判并不是金代儒 学的独创。早在唐代中期,就出现了针对传统经学模式的 疑古批判思潮,如中唐的《春秋》新学。到了金代,儒家 学者们不仅没有改变批判疑古的学风,反而由于政治负担 较小而强化了批判精神。金代儒者的批判对象集中于秦汉 以来的儒家主流思想,其中,对以孔颖达为代表的传统经 学和二程代表的北宋洛学的批评最为严厉、突出。李纯甫 秉持统摄儒佛的态度,我们可以在《鸣道集说》中摘出二 程排佛言论76条。另一位金代经学家王若虚也在《五经辨 惑》等著作中摘引二程观点达21次,据刘辉考究,其中只 有3次对二程的解经之说表示了有所保留、不完全的肯定 和赞同,4次客观介绍、无赞无否,其余14次全为批评和 否定。由此可见金儒对二程学说批判之激烈。王若虚继承 了中唐以来的经学传统。他解经重实,排斥曲解经文、违 反人情常理的解经方式。他批评汉儒和宋儒为“陋儒”。 自中唐以后,汉学及其传统的师法、家法被逐渐遗弃,传 统方法“疏不破注”也被贬低。而“疑古惑经”“舍传求 经”“以己意解”的解经方法逐渐盛行,王若虚的《滹南 辨惑》便是最好的证明。对于自汉以来的诸儒观点,王若 虚不仅旁征博引、有议有评,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见 地。由于他经学、文学、历史兼治,三者互相影响,他的 见解和主张具有新意。可惜的是,由于王若虚的著述大多 佚散,其经学批判思想显得松散而难以把握,但这并不影 响其经学成就的高度。
综上所述,回顾唐代经学对金代儒学一百余年发展的 影响:首先辅助统治,其次充任制度,而后引导其自由发 展,取得了学术上的长足进步。金代儒学在中国儒学发展 史上,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起着承前启后的作 用:前承完整的唐代经学体系与未发展成熟的北宋道学, 后接南宋理学北传开启崭新的元代儒学。这与唐代经学 所处的历史地位亦有相似,后者上承汉学,下开宋学。这 对“师徒”都以思想发展的中介或桥梁的形式完成了自己 的学术使命,实现了自己的理论价值。回顾唐代经学对金 代儒学的影响,不仅仅是要说明学术思想发展的自在连续 性,更重要的是要牢牢确立金代儒学在中国儒学史的重要 地位,也就是说,要肯定金代思想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 要地位。金代儒学不是独立隔绝的(不否认其有独创的部 分,任何一个时期的思想都有其独创性),其在中国古代 思想共同体中的地位正如同女真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 的地位一样,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是集体中熠熠生 辉的独特个体。
责任编辑:史偌霖
原文地址:http://www.whcyzzs.cn/html/2023/0529/172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