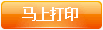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后稷网 > 文化产业网 文旅
乡村文化建设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以产业化为“有效经济”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以文化内核为“有效治理”的关键手段,对突破“胡焕庸线”的既有产业空间格局,实现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可持续化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乡村治理文明变革提供了动力。现通过对湖南省L县文化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实践现状的分析,总结乡村文化产业建设发展经验,提出文化产业助推乡村文明重塑的实现机制。通过文化产业化的发展方式,在满足原住民对乡村文化的情感依恋中寻找新的平衡,在改善居民物质生活的基础上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精神动力,从而实现传统乡村文明向现代乡村文明的历史性转变。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以及新型城镇化与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乡村人口结构、产业结构、文化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城市发展中的虹吸效应一方面加快了大型城市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中小型城市及乡村发展吃力的局面。
费孝通曾提出,都市的兴起和乡村的衰落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中国的传统村落是一个由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因而非农化和工业化或许可以使其发生裂变,但不会使其成为“村落终结说”的必然[]。传统村落中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缩影,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在空间上的存留,村落的转型发展同样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在现代社会中转型发展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乡村文明的载体。”[]要想留住中华民族文明的根,就必须使村庄在保留乡村文化符号的基础上留住人心。
片面的产业发展虽然能够在短期内带来表面物质层面的改变,但工业发展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资本积累对淳朴民风民情的消极影响、原住民无力持续发展易致“返贫”等问题层出不穷,可见现代化因素的盲目使用实际是对村庄自身力量的解构。胡惠林认为乡村振兴的关键与核心是重建乡村文明关系和乡村文明秩序[]。在“后乡土时代”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应给予传统生存上的空间和文化在空间上的载体,而并非简单利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价值观念并以“倾倒”“灌输”的形式“强加”给乡村。
在乡村治理中通过文化产业化的发展方式,找寻原住民的现代化需求和乡村文化原生性的平衡,既是乡村文化产业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乡村文化振兴在发展过程中正确的路径选择。在建设乡村文化产业的同时,培育人们的精神力量和文化信仰;在改善居民物质生活的基础上,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内驱的、可持续的精神动力;在文化责任、文化使命与经济目标之间能够寻求一种平衡,从而突破既有的物质生产资料与精神生产资料不平衡的“胡焕庸线”,重塑乡村文化自信,形成更加有利于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文化产业结构。
湖南省L县文化产业推动乡村振兴实践现状
湖南省L县位于湘中偏西南,有汉、回、瑶等24个民族。2018—2020年L县国民经济发展趋势向好。近年来,随着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L县逐步将地缘劣势转变为环境优势,通过整合利用辖区内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名人等资源推动农业特色产业、文化旅游业发展。从经济数据来看,其文化产业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功,但在实际调研中发现,其现有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存在较大隐患。
文化资源浅层开发缺乏长期动力
以S镇对魏源的开发为例,当地政府在规划中缺乏科学认知和经济主动权,资本在建设的过程中以快速资金回笼为目标,导致文化资源被表面化、浅层化利用,缺乏资源核心竞争力,无法形成长范围辐射吸引力。其结果往往在“脱贫”目标完成后后续发展无力而导致经济停滞。当政府为政绩驱动,将经济指标视为乡村振兴的主要构成,则会从政策角度忽视文化资源本身的价值,从中观层面加速资源内涵的解构。当村民受企业影响,以资本逻辑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建设与发展,将乡村丰富且独具特色的文化作为获取短期经济效益的手段时,经济利益至上的观念则从微观层面对乡村核心价值观念进行消解。其最终结果往往是短期经济快速增长、短期行政目标达成、乡村传统价值体系断裂、乡村文化再生能力下降,最终导致乡村振兴文化产业无法可持续进行。因而乡村振兴要从根本上通过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实现,应该是在乡村本位下对传统村社的理性重建,并在此类集体价值观念的约束指导下进行产业化建设。
资本介入冲击传统乡村文化
从产业化建设的角度看,X村文化产业建设充分利用了行政本位下能人带头作用、政府与资本利益互换,打造了当地文化产业特色名片,在短期内完成了乡村基础设施和文化娱乐项目基础建设,实现经济效益正增长;但从文化塑形的角度来看,其文化产业发展实际是资金注入的文化空心化的经营。资本的大量介入让原住民本能趋利,商业色彩冲击着乡村文化原有的质朴本色,对当地原生态的淳朴民风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
辐射带动作用与村际马太效应之间存在悖论
资源有限性往往造成村际之间起点失衡、发展动力失衡等问题,从理论上来说,通过资源集中、重点建设、向外辐射可实现“先富带动后富”。然而在实际情况中,由于政策驱动、资本逐利性,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村际马太效应,通过政策倾斜聚集优势资源的村庄在发展后所形成的虹吸效应远大于辐射作用,形成“产业扶贫悖论”[]。“明星村”往往获得更多利好政策、文化资本和社会关注,发展驱动力较足,村际之间贫富差距扩大,在客观上压缩乡村文化的生存空间,拉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经济差距的基础上极易构成文化认同危机,使乡村文化逐渐失去从容的文化自信语境。
乡村文化建设发展的经验与反思
脱离经济发展的文化振兴缺乏实际意义
文化以意识形态形式存在时,属上层建筑范围,由经济基础决定,文化的发展与新乡村文明的塑造是建立在新的历史阶段乡村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在经济上缺乏话语权的主体也很难具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农民作为乡村文化的创造者、建设者和传承者,其对乡村文化的认知水平、认同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乡村文化的未来。因而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实现文化振兴,促进乡村发展,不能从意识形态角度阐述文化的力量,也不能从城市的角度理解乡村,更不能从学术理论的角度以傲然的态度空泛地指导政策制定。在乡村振兴中要从“看得见,摸得着”的角度出发,将文化的经济效益阐述清楚,使乡村居民明白文化不是虚无缥缈的,文化也可以改善实际生活。
脱贫后乡村治理需要重塑乡村文明
乡村文化振兴需要新时代乡村文明对乡村文化自信的重塑。传统乡村文明是农耕文明与农业社会历史塑造的一种文明体系[],现代乡村文明则是传统乡村文明在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中产生的。经济上的脱贫存在“返贫”风险,只有从根本上完成对基层乡村的文明性变革,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文明中的惰性思维和落后思想观念,才可以实现乡村文明的重塑,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
以文化为核心的产业化建设实现乡村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同构
拥有独特个性的乡村文化,始终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具多样性的文化资源[]。以经济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容易造成文化主体价值观念的嬗变,消解乡村文化中质朴的文化品质。要想克服奥尔森所谓的“集体行动困境”,则需借助文化的力量,在血缘认同和坚守村社意义的基础上达成村社理性[],通过紧密的个人关系和相互信任来引导成员进行自愿合作,以文化力量对冲市场经济导致的“理性化”“个体化”“原子化”,以减少交易成本[]。
文化建设中乡村文明重塑与再生的实现机制
依托文化资源,建设文化产业
长期的城乡二元发展格局,经济的滞后使乡村原住民对物质向往与追求的迫切程度远高于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因此政府应使村民主体认识到文化同样能够通过产业化路径带来实际的经济收益。
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文化产业因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资源掌控程度、个人认知能力等的限制而存在较大的权力分配不公现象[]。通过文化产业发展建设,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还权力于村民,使其认识到自身所拥有的文化权力,缩小与城市在精神与经济层面之间的差距。
如果说物质上的差距是先天不足,那么精神上的发展、文化上的建设则是“弯道超车”的最佳契机,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则正是契机与实际相结合的最优路径。文化产业是在传统文化生存场域中、村社理性建立基础上内生发展的。被城市人视为精神消费对象而为农村带来经济收益的,恰恰是乡村区别于城市工业化景观的自然环境、安逸的生活、淳朴的乡村民风所蕴含的美学价值与人文价值。文化旅游业项目与短视频内容创作将城市人民对乡村生活的向往和消费者的猎奇心理转变为产业经济,但需要注意的是乡村主题短视频的制作不应是以资本投资为起点、商业变现为终点的短期项目,而应该实际把握住互联网平台矩阵,将乡村真实生活映入大众眼帘。
立足文化教化,提高乡村文化认同度
人是文化认同的主体,村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程度是其对乡村文化所蕴含的价值观念的理解和认可,乡村文化认同感的缺失是乡村文化力量被消解的主要原因。对于乡村而言,要重视的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文化风气的教化,通过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构建人与人和睦互敬、彼此尊重、谦逊有礼的乡村文化价值观念,使其具备回望历史,对照现实的能力,从而对农耕文明下的中华文化具有更深刻的认知。在此过程中,尤其要重视对青少年群体乡村文化认同感的塑造,将文化教化融入日常教学中,提升青少年对乡村风土人情、手工技艺等文化资源的认知水平,使其知晓乡村文化的内涵。
激发内驱动力,重塑乡村文明
行政本位下仅依靠政府与资本的力量容易导致村民形式化参与、供需错位、村际差异扩大等问题,通过建立村社理性实现村民自我治理,树立良好乡风是克服此类问题的最优路径。村社理性、良好乡风的发挥需要能人带头引导建立。村社理性发挥作用的基础往往建立在“弱流动”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导向、舆论宣传等唤醒原生的文化基因,使对该乡村有深刻感情的人才回到乡村进行建设。以舒适的自然环境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为特色,吸引退休人群、艺术家等“新乡村阶层”落户乡村,为乡村带来现代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在与原住民生活观念、生活方式的碰撞与交融中催生新的乡村文明。
当生产力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时,如何变革生产关系使其与生产力相适应是中国在发展现阶段所遇到的关键问题。乡村振兴始于产业发展,实际上是对广大农民价值观念和思想认知的重塑,也是乡村文明在现代秩序体系下的重塑。
在现代工业化进程下,对物质的追求难免根植在人们心中,文化振兴既包含了物质层面的经济获益,同时重构了农民的整体精神文化面貌。这需要有长期规划的眼光并徐徐图之,产业化是“有效经济”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文化内核是“有效治理”的关键手段。政府既要认识到文化产业振兴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实现方式,又要在改善的过程中警惕资本的一蹴而就,做好规划、引导、管理工作,将乡村资源、人才的力量切实发挥出来,如此才能激发乡村文化产业的内生动力,推动乡村文明实现现代化变革。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EB/OL].(2021-05-11)[2022-10-10].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2106/t20210628_1818826.html.
[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田毅鹏,张帆.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体制性影响因素新探[J].社会科学战线,2016(10):170-178.
[4]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2(01):168-179+209.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6][8]胡惠林.乡村文化治理:乡村振兴中的治理文明变革[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0):62-75.
[7]叶敬忠,贺聪志.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为例[J].中国社会科学,2019(02):137-158+207.
[9]邵晨.乡村振兴不可忽视乡村文化力量[J].人民论坛,2018(26):130-131.
[10]田阡,阳姗珊.乡村振兴视域下村社理性与个体理性何以共存——基于云南一傣族村寨的田野考察[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0.
[11]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社会行动(增订版)[M].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2]胡惠林.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理论·政策·战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史偌霖
原文地址:http://www.whcyzzs.cn/html/2022/1128/121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