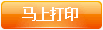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返回原文
返回主页
后稷网 > 文化产业网 文旅
乡村旅游解说中的游客体验,历经乡村文化认知至乡村文化认同的构筑过程。由于解说的信息交互性和乡村文化的根性特质,解说语境下的游客乡村认知具有历史志书的认知特点,使乡愁记忆往往重构为生命感悟的历史记忆。乡村文化认同较之游客地方感知,更强调生命关怀与家国情怀,成为具有阈限性的旅游真实性体验和超越个体文化差异的族群认同体验。乡村文化认同是一种民族文化归属心理,认同构筑中碎片化乡愁记忆向系统化历史记忆的追溯,对家国认同构筑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传承与创新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作为具有普泛意义和本土特色的文化研究范畴,包含长期农耕实践中积累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其遗产的文化内涵须由体验而知,其遗产的文化传承须由文化认同者担负,因此,基于体验的文化认同构筑成为乡村文化传承的心理基石。旅游作为调节身心的文化体验活动,其体验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体验的衡量基准,历来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之一。将乡村旅游体验的衡量基准与文化认同相关联,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的共生模式,提升文化认知。
研究概况
解说体验与文化认同
认同(Identity)的概念语意较多,文化认同具有认可和赞同文化之意。作为一种肯定的文化价值判断,文化认同是发自本心的文化自觉行为。乡村文化认同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研究内容集中于乡土志书的历史书写、乡土文学的乡愁记忆、乡土意识培养等方面。其中,强调文化认同构筑实践的应用型研究主要集中于乡土教育领域,当下教育传承路径已成为研究热点。国外相关研究中的乡村教育传承研究,不仅涉及学校教育,还论及旅游解说。以文化教育和遗产保护为主旨的解说称为遗产解说,具备完整的研究体系。
解说(Interpretation)研究起源于美国,是从解说员的职业探讨衍生出的应用研究。1920年,Enos Mills首先运用“interpreter”一词描述洛基山的导游,强调这一职业的解说特征。1957年,“解说之父”Tilden在《解说我们的遗产》一书中构建解说核心概念,“解说并非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一项通过原真事物、亲身体验以及展示媒体来揭示事物内在意义与相互联系的教育活动,是对事实陈述背后更大的真相的揭示”(Tilden,1957)。这一概念对文化阐释和教育活动的解说特征归纳有效地指引了后续的研究。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PS)延续这一观点,将解说界定为“游客自身认知与资源内在意义间的交流过程”,强调以文化认知为中心的解说体验探讨。借用认知理论解构解说过程的“传递者—信息—接收者”模型,强调信息传播技巧和信息传播媒体对游客体验的正向作用。模型构建标志着解说研究从质性描述转入量化分析,但模型构建并未割裂阐释文化的解说研究传统。Robb发表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的论文着重探讨了亚瑟王传说在英国乡村旅游解说中的呈现过程,以及Cornwall地方文人、院校学生参与解说的影响。Ashworth对欧洲遗产解说的研究,着重强调欧洲地域文化解说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
乡村旅游解说与乡村文化认同
乡村旅游解说的对象是乡村,将乡村景观划分为建筑、民俗、精神三类,对应景观符号的能指和所指,虽然作者仅用寥寥百字介绍观点而未铺陈,但这一尝试不失为突显乡村性的解说尝试,并对村落共生演化模式的探讨产生了积极作用。强调“突出乡村景观,以社区居民为讲解媒介”的解说系统构筑。从旅游规划角度探讨了江苏乡村旅游解说的产品体系。总体而言,如何在乡村旅游中既发挥解说的文化教育与文化传承功能,又借助解说提升旅游体验,是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时间与空间:乡村解说的叙事逻辑
乡村的知识考古
解说文本是旅游资源与游客认知交互的媒介,文本对地方文化的知识考古是旅游者认知乡村文化的前提。“知识考古学”一词来源于福柯,强调以历史主义态度对文化进行溯源性结构探知。“乡”是最古老的基层单元之一,《说文解字》解释为“国离邑,民所封,乡也”。后由“乡”衍生出“乡里”“乡籍”观念,表示政权管理下的地域归属,历史上的人口迁徙和人口流动又强化了“乡”所表现的地域认同感。土与农耕密切联系,物随土产,生命依赖土地的赐予而繁衍生息。乡、土二字合用,以一种独特的地方文献存留于世的乡土志诞生于晚清。晚清乡土志编纂,一为搜集地方文献资料,二为推行新学以提升国民素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诏令各省督抚将各省、府、厅、州、县的各类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各种学堂,兼习中西之学。同时,从培养儿童热爱乡里、热爱国家的思想出发,积极开展乡土教育。光绪三十一年(1905),学部颁布《乡土志例目》,以地理、历史、格物作为乡土志编纂的基本体例,规定乡土志的类目为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民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十五门,要求事详而文简,词雅而意明。这一体例较之府、州、县志,删繁就简,更趋近历史上关注风土人情的风土志体例。
风土志是古代地方志书的重要门类,由来已久且多由名家私修。“风”涵盖地方社会的历史认知,记录建置沿革、节令习俗、信仰观念、人物传记、历史掌故等。“土”代表地方社会的地理认知,山川形势、街道巷坊、桥梁驿递、风物特产,无一不由土滋养而生。生命关联风与土,是风土志叙事的主旨。风土志以物质生命为叙述起点,以人之生命为叙述归属,强调群体生命相沿成俗,个体生命历练为贤。风列于土前,体现出地方文化以礼俗传承为主的传承特质。晚清风土志向乡土志转型,传统体例删繁就简,适当增加格物内容,体现出吸纳西学和格物致知的认知态度。这一转型正是知识分子在变革图强背景下将地域认同、生命认知凝练为家国情怀、民族认同的社会实践。费孝通先生的乡土研究融入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关注我国乡村文化的农耕性及浸润于泥土中的根性,在根性溯源中对生命的关怀使我国乡村文化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民族性特征。《乡土中国》丰富了民族文化的本土内涵,使乡村成为具有民族印记的文化符号。
乡村文化虽因地域差异而各具特性,但历史上长期延续且具共性的方志纂修体例却是了解文化共性的一把钥匙。地方志的乡村认知,将生命认知贯穿于认知始末,形成生命于时、空二维拓展与延展的活态认知。这一认知是否适用于乡村解说,笔者将借助传统村落——漆桥的个案继续探讨。
乡村的空间结构
历史认知首要解决起源与流变问题,起源与流变的过程性经历则往往保存于地名之中。漆桥位于南京市高淳区,为中国第三批传统村落,村民以孔姓为主,相传为孔子54世孙后人,繁衍至今。漆桥村以桥命名,相传汉丞相平当筑桥河上,施以朱漆,遂有漆桥。此处又名南陵关,明中期以后因水运商贸流通形成关隘码头,又因商品交换量日益增长,村落空间逐渐沿河道自然延伸拓展,成为高淳东北部的重镇。据当地老人回忆,“今南陵关所在地,原有孝子牌坊一座,清代时村上出过一位进士,为报母恩,立有孝子牌坊一座,民国时期因改建银行而拆除”。今村北不远处仍有双牌石地名留存。地名记录了村落发展演进的基本脉络,并将此演进脉络保留于漆桥、南陵关、双牌石等地名之中。
乡村解说将乡村地理与乡村历史相结合,赋予村落孕育和滋养生命的文化意涵。漆桥古村的设计者究竟为何人今已无考,但孔氏族人至迟在南宋已迁居于此,安土重迁的农耕传统决定孔氏族人必定在村落建设中不遗余力。主街是村落公共空间的核心,村口处的节孝牌坊、村中的宗族祠堂、村尾的保平古井沿着主街间隔有序分布,无不强调着生命孕育于家庭、有井之处即有乡、有乡之处即有家的生命认知。田野调查中发现,旅游者并未过多关注村落起于何时,西汉、南宋,抑或明清,甚至认为平当的事迹难免有虚构之嫌,但对村落经由水运码头变迁而来的发展历程,以及村落聚族而居的繁衍生息状况,仍表现出较高的认知热情。
乡人、乡物、乡俗:乡村解说的叙事对象
乡人的历史叙事
乡人是乡土社会的个性符号,乡人掌故则是村落历史的文化标记。以江苏省为例,现存的26处中国传统村落中,三分之二以上保存着乡人和乡族的历史掌故,或以孝行、或以善举、或以文苑名列乡间,其事迹或存留地方文献,或口耳相传,需经田野调查而得。解说对乡贤事迹的挖掘和整理,既有赖于文献又不同于文献梳理。
聚族而居是传统农耕社会常有的居住形态,乡人的历史叙事又往往关联乡族的历史叙事。民间故事《孔文昱娶妻赚山居》,既是关于开基祖孔文昱的历史叙事,又是漆桥孔氏族人的历史叙事。
游子山北部有个村庄叫者(za)家桥,这里有个姓诸的员外,号称“者百万”。一天,孔文昱流落至此,虽衣衫褴褛,难掩其清秀眉目。者百万听闻孔文昱颠沛流离的身世后,觉得他十分可怜,顿生怜意将他留下,让他在家中做长工。孔文昱到了者百万家后,十分勤快。一天,他帮者百万洗脚,者百万说:“你要小心,我脚底长了一根红毛,算命先生说我的百万家私都因它而起。”孔文昱不以为然,说:“这有什么,我两只脚底各有一撮呢。”者百万一看果真如此,觉得孔文昱将来一定会富贵,就把女儿许配给他。结婚后,者百万给了小夫妻一座小山,两人就在山上搭了三间屋子。
者百万死后,他的两个儿子请风水先生看墓地,风水先生说,若将者百万葬在村前的小山上,者百万的后人可以做官;若葬在村后的小山上,则后代子孙多。兄弟俩一商量,要多子多孙,便说要葬于后山,可后山者百万已经给了孔文昱一家,并且立了字据。孔文昱叮嘱儿子,以后把自己埋在后山上。自此,孔氏繁衍生生不息。
“娶妻赚山居”的叙事保留了孔文昱落籍高淳、入赘者家的历史情节,并沉淀为孔氏族人共同的历史记忆。叙事中聪明、勤劳、善良等人物评价词汇既是个体评价又是家风颂扬。叙事结尾的两可选择设计看似选择风水,实则选择价值观念,高官厚禄与多子多孙的两难选择中,孔氏先祖选择了后者。口耳相传的乡土掌故将家风观念代代相传,个体生命终有尽头,子孙繁衍则生生不息,倡导了生命延传和子孙绵长的生命观念。对家族历史掌故和乡人事迹的历史叙事,使旅游者可以更客观地解析家族和个人的境遇变化,激励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旅游者保持探知生命的热忱,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乡物的历史叙事
解说叙事除依赖历史文献外,有形物件如牌坊、民居、宗祠、桥梁等村落标志性建筑也是解说叙事的重要载体,蕴藏于建筑中的历史记忆借助解说释放而出。苏州陆巷古村被誉为“太湖第一古村落”,提及陆巷必谈王鏊。王鏊是明代著名经世之臣,曾任正德时期内阁首辅,民间俗称“宰相王鏊”。古村中的标志性建筑三元牌楼,建于明成化十年(1474),清道光六年(1826)重修,分别是探花牌楼、会元牌楼、解元牌楼,三牌楼呈丁字型排列,是王鏊在科举中所获功名的标志。牌楼自1474年保存至今,历经500余年,乡民对牌楼的呵护和保护,体现出当时对科举文化的尊崇。王鏊是明弘治中兴的重臣,官历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为官期间,勇除八虎,清正朝纲,其事迹深入民心。寓居乡里期间编纂的地方文献《震泽编》,成为记录苏州地方文化的重要史籍。牌楼承载的不仅是逝去的科举功名,更承载乡民对治世能臣的崇敬与怀恋,对文化名人的追思与仰慕。逝者已逝,生命却在纪念建筑物的不断修缮与保护中得以永恒,怀旧乡愁经牌楼解说重构为乡贤崇拜,成为联系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
乡俗的历史叙事
个体生命历练为贤,群体生命沿袭成俗。如果说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是常态化的时间生活,岁时节庆则是节点化的时间生活,以狂欢表达日常,实则要借助狂欢来表达一种不同常规的生命态度,借助仪式强化历史记忆,传承价值观念。
岁时节庆多随农耕节律而生,亦有对历史人物或民间传说人物的纪念。社庙常奉于里社之中,颇具地域性、民间性、草根性。如“祠山大帝”“东平王”“刘猛将”“金龙四大王”“晏公”等,或司水运,或掌农耕,或守护一方。随着近代礼俗改造的开展,乡村庙会所依存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宗教色彩不断减弱,歌舞娱乐和商品交易的社会功能不断强化。“祠山大帝”名张渤,相传为西汉人,因治水有功,造福一方百姓,后人立庙祀为“水神”。祠山崇拜广泛流传于南京高淳、溧水以及安徽宣城、广德等地,“祠山大帝”执掌河运,舍己为人,其不辞劳苦开凿运河的传说故事深入人心。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祠山神职亦由河运执掌,进而延伸为乡土守护,成为文化认同的标志。
南京高淳地区乡村旅游的开发,客观上促成了祠山庙会歌舞娱乐与观赏油菜花游览活动的结合。既保留了祠山庙会中的巡游仪式特点,又保留了巡游队伍中的抛钢叉、走高跷、挑花篮等歌舞娱乐表演形式。祠山装扮物行头以魁头和脸谱最具特色。为祠山而舞的傩舞表演不仅展现求财避祸的价值趋向,不同颜色的脸谱面具还代表不同的道德评判,黑脸的祠山代表正直、勇猛,红脸的猛将代表忠勇、侠义。在溧水祠山庙会中,祠山被扛抬于蒲塘桥中,回头守望青苗的巡游仪式,正是乡村情结的寄托所在。当仪式借助象征性物件和程式化活动表达戒争讼、崇正直、尚勇猛等价值观念时,仪式不仅是歌舞娱乐,而且成为对生命态度的表达与传承。
生命感悟、家国认同:乡村解说的叙事主旨
认知是构筑认同的心理基础,记忆追溯是实现认知向认同跨越的必由之径。乡愁是旅游者出游乡村的情感动机,其情感来源:一为城居者的田园怀恋,一为离乡者的故乡怀念。前者表达崇尚自然的意愿,后者是人与事的乡俗怀旧。这一崇尚与追忆往往基于个体经历,既具有焦虑与憧憬的自然心理特征,又具有碎片化记忆的特点。然而“记得住的乡愁”并非总是伤感和碎片化的,若将乡愁怀旧与家园依恋置于历史主义的知识考古中,则不难发现,乡愁的历史记忆应有另一种特色鲜明的主体色调——生命感悟,个体生命历练为贤、群体生命沿袭成俗。历史文献、历史纪念物以及延续而传的民俗仪式构成了历史记忆的记忆之场,乡村解说借助记忆之场完成记忆追溯,重塑碎片化乡愁。
集家而成乡:家的组织观念泛化
从节庆仪式传承的组织基础来看,结构相对稳定的农村家庭组织是仪式传承的重要组织基础。南京高淳、溧水,常州溧阳等地的外流人口,大多为“离土不离乡”的短距离外来务工者,其定期返乡频率较高,且与乡村生活关联密切。加之高淳等地聚族而居、多世同堂的家族传统,更奠定了老人会等家族联合体在节庆仪式传承中的独特地位。随着特色乡村的发展,高淳、溧水、溧阳等传统农耕区中的农业产业链和旅游产业链进一步延伸,更多乡民实现了农业就业与旅游就业之间的不定时转换,而个体家庭的发展和家庭成员幸福指数的增加将有助于家庭成员关注家乡民俗和延续传承文化谱系,热爱家乡。
集乡而成国:乡的地域观念泛化
“乡脚”构造的变化使文化空间出现分层,一是原有村落基础上以蒲塘桥为中心的祭祀圈,一是新型社区中以博物馆和市民广场为中心的公共文化圈,两个圈层间的文化交流通过旅游活动来实现。溧水举办乡村音乐节时,天生桥博物馆前的广场上举行了祠山出巡仪式展演,参与者大多来自原洪蓝镇的蒲塘村等地,年轻一代在重构的“乡脚”中延续着民俗仪式,其对“乡脚”的地域认知已扩展到县、市甚至更广的地域范围。
记忆的追溯与重构对认同构筑至关重要。解说将游客借助视觉形成的景观具象和借助听觉形成的景观意象合二为一,形成以生命为主旨,以时间为主轴的历史记忆。碎片化乡愁记忆逐渐重构为关于生命感悟的乡村记忆。由个体生命到群体生命,由村落变迁到社会变迁与国家命运,家国情怀油然而生。在由此及彼的推演过程中,旅游解说将旅游者对乡村认知所构筑的碎片记忆规整为对生命和家国的历史记忆。当历史记忆向更具现实感的社会记忆转换时,文化认同也将构筑于共同的族群记忆中。
同时也应关注到,旅游者对乡村文化认同的体悟程度往往受自身生活阅历的影响,生活阅历的增长又常与年龄增长正向相关,然而年龄增长并不是决定性影响因素。“家庭团”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往往存在跨越辈分的代际沟通,即年长者给年少者讲述生活阅历后,年少者的乡村体验度明显提升。此外,旅游者受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以及社会职业等多元因素的影响,其乡村体验也呈现出层次差异。
“乡”是最古老的基层行政单元之一,由乡衍生出“乡里”“乡籍”,体现出地域认同的观念意识。村落展现了人类聚集而居的聚落形态,既是生产单位又是休憩之所。乡村文化认同包含了地方认同感、满意度、忠诚度等心理情感,同时较之前者更具价值导向和民族精神内涵,应成为乡村旅游解说体验的衡量基准之一。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看,旅游解说是一种传承文化的叙事行为,因而乡村解说往往兼具文本和情境两种叙事方式。解说语境下的游客乡村文化认同,历经认知、记忆再到认同的建构过程。经由历史志书的知识考古建立乡土文化认知,借助乡人、乡物、乡俗的历史叙事重构碎片化乡愁,最终构建以生命和家国认同为核心的乡村文化认同。因此,具有主旨的旅游解说有助于探索乡村文化传承与乡村旅游开发的共生模式,丰富文化的旅游型生产和传承路径,提升民族文化认知。
参考文献
[1]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J].历史研究,2003(04):68-84+190.
[2]凌宇.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中的乡土意识[J].文学评论,2000(04):18-24.
[3]季中扬.乡土文化认同危机与现代性焦虑[J].求索,2012(04):162-164.
[4]谢治菊.转型期我国乡土文化的断裂与乡土教育的复兴[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2(04):156-161.
[5]罗芬,钟永德,付红军.SMRM模式在环境解说中的应用初探[J].桂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05):40-43+48.
[6]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7]冯淑华.基于共生理论的古村落共生演化模式探讨[J].经济地理,2013, 33(11):155-162.
[8]吴必虎,金华,张丽.旅游解说系统研究——以北京为例[J].人文地理,1999(02):32-34+69.
责任编辑:史偌霖
原文地址:http://www.whcyzzs.cn/html/2022/0726/1141.shtml